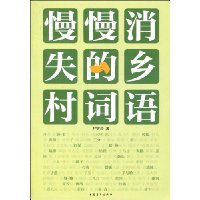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 |
 |
|
 |
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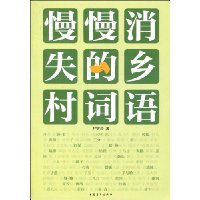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页码:246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
·ISBN:9787500687740
·条形码:9787500687740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讲述了我从十几年前的一个黄昏开始迷恋乡村。乡村是人群聚集的地方,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息繁衍,传说繁密得像天上的星星。我在日落黄昏的大堤上闻到了乡村的味道,是从声音引起的。邻居家养的牛母子在这个黄昏经历了生离死别,小牛被人牵走了。母牛从那个黄昏开始号啕,一声接一声地,一声比一声凄惨地,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我只要想到那头牛,眼眶还是湿的。牛哭了三天三夜,我三天三夜没有睡好。我发现那种味道会从房屋、树木、人群、家畜、农具、粮仓里溢出来。味道有些古旧,有些残破,可却让我迷恋。我在思考我迷恋的是什么,很久以后我给了自己答案:我迷恋一个叫乡村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到很远的地里干活,累了就坐在地边田垄上,天马行空地想很多事。天地广阔无垠,田野碧绿有声,可我的心却像干渴的禾苗一样卷曲着,不知如何让她舒展。
乡村在我的感觉里很重要,可我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我不能把她像只苹果-样装进兜里。不能把她像盘缝纫机-样带进城市。而且,她也不可能变成一份嫁妆……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为她写一本书……所以许多年后,我仍需要走出城市去看她。开始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后来我发现任何一座乡村都可以慰藉我。最老的一棵树,或者废弃的一口水井。这里与那里没有什么不同。狗看到生人都要狂吠,天空飞翔的鸟有着相同的名字。树下坐着的老人都有相似的面孔。他们恬淡地述说着时光和岁月,为一场春雨或一场瑞雪咧着没有门牙的嘴。
乡村是什么?是母亲。是根。是精神。是灵魂。还是爱人。
作者简介 尹学芸,女,1964年生于天津市蓟县。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难得浪漫》《女人是祸水》等。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
编辑推荐 《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开圈
新宿
看青
场头
打尜儿
抡火球
出河工
扎王八
翻坑
爬瓜
打头儿
看燕子
推碾子
锔盆锔碗
工分
小喇叭
癔病
打黄狼
烧窑
采菜
车把式
捡麦穗
玩打仗
赤脚医生
炭火盆
热炕头
跳房子
饭瓢儿
汆子
炕席
砸锅
讲古记
开裆裤
姑姑鞋
盘缠
上马子
打夹纸
踩垛
盖顶
梢门
措笆篱
铬豆床
跟脚儿
过庙
打尖
鸡蛋头
搬工
土牛
风箱
加工厂
彩礼
干亲
猪胰子
桑木扁担
念喜
捡粪
六奶奶
相好
针线板
地盆子
柴鸡蛋
砸坷垃
打夯
洋取灯
铁板大鼓
手扶拖拉机
玻璃锤儿
贴饼子熬小鱼
白汗褐儿
手推车
屎瓜儿
赶拉轨子与哈巴狗子
黏火烧
猜撞客
自留地
渡口
跑冰
毽儿灯
鬼剃头
干亲
猪胰子
桑木扁担
念喜
捡粪
六奶奶
相好
针线板
地盆子
柴鸡蛋
砸坷垃
打夯
洋取灯
铁板大鼓
手扶拖拉机
玻璃锤儿
贴饼子熬小鱼
白汗裼儿
手推车
屎瓜儿
赶拉轨子与哈巴狗子
黏火烧
猜撞客
自留地
渡口
跑冰
毽儿灯
鬼剃头
散转儿
杠头
轮官马
摸河底
四合
交公粮
夜战
薅苗
弹弓
刨白薯
抄藤子
猖姆
平整地形
八碟八碗
压箱底
蒺藜狗子
打韧头
合作社
表演唱
捋榆钱
贫下中农
……
序言 家乡被一条河流三面环绕,在平原和洼区的交汇处,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
儿时的记忆经常凸显在某一种状态下,似光那样清晰,而又似雾那样模糊。走在村庄里,经常有某一种触动像琴弦一样能发出响声,那是对故去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场景、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的怀念。那种怀念是尖锐而又绵厚的,带着长长的哨音。那些已经消失的,或正要消失的,或迟早都要消失的词语,其实不单是词语,而是它们涵盖的事物本身,不经意间,都在历史长河里堙没了。在虚妄里,我甚至觉得它们应该走入轮回。只是,我们看不到这种轮回的复生。它像尘埃一样在岁月的经轮里旋转,谁都看不到它,但它们自己能看到自己。
于是我萌发了写《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的想法。开始只是三篇、五篇,因为给报纸写专栏的关系,凑七篇都难(报纸每次连续发七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无穷无尽,而这种无穷无尽恰是乡村智慧的赐予。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我走遍了县境内的许多村庄,寻找和触摸那些存在与过往。与数不清的人在曾经的碾道边或水井旁,在田垄上或场院里,交流和探讨那些属于乡村文化范畴的元素和符号。只能说,那是一口愈挖愈清凉甘甜的水井,它甚至有一种魔力,吸引人从一走到十,从十走到百。
百篇短文即脱胎于此。
许多章节都是信手拈来,即无需筹划,也不用构思。它就在大脑皮层的某一处沉睡,既有现成的人物,又有现成的故事。可有些遗憾也让人莫可奈何。比如,我写到一种棋艺“看燕子”,写它是因为有故事,好写。
文摘 “车把式”是队里的老大。
队里最值钱的家当,当数那挂马车了。当然不单指车,还有拉车的那三匹马。老马驾辕,两匹二青子马拉套。车当然不止一挂,还有驴车,还有牛车。但驴车和牛车都只能干些零碎活,所以赶驴车和牛车的人都不能称“把式”,他们只能叫赶车的。赶马车的人就不同了。“一等人跑外交,恒大烟卷嘴里叼;二等人赶大车,小鞭儿一摇一块多……十等人上海河,小车一推没有辙,两季不去没法活。”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民间流行的顺口溜,都是社员凑在一起编着玩的,属自娱自乐。车把式的地位甚至高过队长,因为每天除了挣工分,还有一块多的补助。过了几年,新的歌谣出现了,赶大车的在十等人当中下排到了第五,可惜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车把式还是一个“上等”的职业,在生产队炙手可热。
大哥从十七岁跟车,有膀子力气,人又勤快,甭管装啥货物,他都让车把式歇着,他干。条件就是他要偶尔摸一摸鞭杆子。大哥天生就是喜欢大牲口的人,喜欢赶大车。两年以后,大哥如愿以偿当了车把式,大哥高兴,我也高兴。大哥第一次出车,是从北山往宝坻拉柿子,我知道马车会从一个十字路口过,就早早跑到那里等他,其实是想看看大哥赶车时的风采。一直等到晌午歪,大哥和他的三匹马拉着的车才跑过来, “得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大哥跟着马车跑,他穿着蓝布大袄,敞着怀,就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大哥告诉我,柿子是给采购股送的,一毛五一斤。这一胶皮车的柿子,上千斤。我问大哥咋不坐在车上,大哥说,他喜欢和马赛跑,马看着他跑,自己也跑得起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