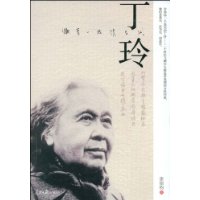|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丁玲 |
 |
|
 |
丁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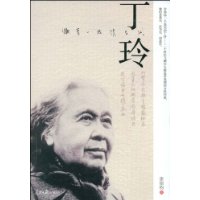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页码:476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
·ISBN:7802087244/9787802087248
·条形码:9787802087248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1975年5月18日。北京秦城监狱。 一条长长的甬道。一名高个子军人走动的背影。一串“嚓嚓、嚓嚓”皮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在长长的甬道里沉沉回响。走到甬道尽头,他向立在甬道里值班的女看守示意,打开一间单人囚室。
高个子军人:“7054号,收拾你的衣服、用品,跟我来!”
囚室里,鬓发斑白、倚在床头看书的老年女囚摘下老花镜,迟疑地抬起头来说:“换号子吗?”
高个子军人:“不该问的别问。动作利索一点!”
女囚怔怔地:“是。”
不一会,女囚提着一个小旅行袋,跟在高个子军人身后,来到一间办公室,低着头立在墙边。
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位五十来岁的监狱首长与高个子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一边用铅笔轻轻敲击着办公桌上的那块大玻璃,一边说道:
“你就是丁玲?坐吧。”
丁玲微微抬起头来,轻轻“啊”了一声,仍站在那里。
监狱首长:“进来五年了吧,嗯。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你被释放了。”
丁玲一惊:“是么?”
那位监狱首长点了点头,又说:“你的问题,专案组已有了结论,因为没有发现新问题,给出路嘛。”
高个子军人走近办公桌。拿上一份早放在桌上的铅印件,对丁玲说:“这是释放通知书,你签字吧。”
丁玲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坐下来伏在茶几上,颤颤巍巍地在那份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轻轻问:
“回北大荒吗?”
作者简介 涂绍钧,笔名柯葳。汉族。1947年6月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中共党员。1964年因病于临澧一中高中肄业后,历任临澧县鳌山完小、柏枝中学语文教师,临澧县文化馆文学专干,中央党校林伯渠传记组成员,常德地区群众艺术馆文学组组长。现为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德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传记文学《林伯渠》、《风雨征程》及丁玲研究专著《走近丁玲》,中篇小说《残月》等;其中《林伯渠》、《走近丁玲》二书分获第二届、第六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死别生离未许愁》一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连载。
媒体推荐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湍,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孙犁
在她的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有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务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邓友梅
编辑推荐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丁玲——二十世纪飞蛾扑火般追求真理的女性作家,她的受难史、抗争史、创造史。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伶仃孤女
第二章 少年叛逆者
第三章 展翅高飞的鸟儿
第四章 闯荡北京
第五章 初登文坛
第六章 出版《红黑》受挫
第七章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第八章 踏上新的征途
第九章 身陷囹圄
第十章 抗争在魍魉世界
第十一章 “今日武将军”
第十二章 初抵延安
第十三章 奔赴抗日前线
第十四章 西战团在西安
第十五章 窑洞岁月
第十六章 转折
第十七章 桑干河上
第十八章 走向世界
第十九章 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第二十一章 到北大荒去
第二十二章 把心磨出厚厚的茧子
第二十三章 太行山下
第二十四章 重返文坛
尾声
后记
……
文摘 第一章伶仃孤女
1
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
两扇漆黑厚重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
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
灵牌后面,黑纱悬绕的镜框里,蒋保黔身着东洋学生服,英俊年少。
灵堂前,八个道士分立两旁,正做法事。
少顷,门外爆竹声骤起。几位绅士模样的人鱼贯而入。
身穿孝服,坐在堂屋太师椅上守灵的死者的两位堂兄蒋保川、蒋保滇起身迎客。
蒋保川:“高大人,张老爷,请,请!”
蒋保滇:“林少爷,王相公,请!秋蝉、菊香,看茶!”
女佣秋蝉等执茶托献茶,众人人座。
绅士甲:“二位老爷,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三老爷怎么这样就——”
绅士乙:“保黔兄英年早逝,可惜,可惜,一个人才啊!”
绅士丙:“可不是?前两年我们去东洋留学,学友中就数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壮志未酬,遗恨九泉哪……”
蒋保川:“多谢各位赏脸。人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办法的。
只是他这样撒手一去一留下孤儿寡母,作孽啊。”
众人作悲戚状,连连摇头。
绅士甲:“三太太呢?”
蒋保滇:“我三弟命里不该绝后,三太太又怀上了蒋家的血脉,在内房歇息。”
绅士乙:“如此说来,我等前来吊唁蒋公,也该给二位老爷道喜了,蒋门祖德阴功,继业有后啊!”
蒋保川:“道什么喜呀,三弟欠下这一屁股账去了,三太太将来拖着一双儿女,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绅士丙:“保黔兄多少给三太太留了几个吧,再说,他名下不是还有三百多石田产么?”
蒋保川:“哼!三百多石,恐怕三十多石还不到了呢。唉,想我们蒋家,世代为官,享尽了荣华富贵,二房的这一份家业,想不到竟败在他手里。你们想想看,他生前虽开了个药铺,自己也常给人看病,遇上揭不开锅的,不但汤药钱全免,还得倒搭上一两块光洋,对吧。再加上两口子都不会理财,家里天天牌九不断,烟灯都要三四盏,坐吃山空,再大的家业也要败啊!”
众绅士听罢,慌了神,忙问:
“那,欠我们的光洋呢?”
蒋保滇:“各位老爷,这个嘛,请尽管放心。他名下虽然田产不多了,还有几十间房产呢,不是钱么?”
蒋保川:“对,也不光是欠各位老爷的,欠我们本家兄弟也不少呢,只要我们有,少不了
……
后记 1979年初,我接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完成一部临澧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传记文学的书稿。3月2日,我来到飘飞着鹅毛大雪的北京。不久,在采访老作家白薇时,得知丁玲刚从山西回到北京,就住在离她家不远的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我想,丁玲和林老是同乡,相信她不会拒绝我的采访。于是,我打电话和陈明先生联系,告知丁玲已住医院。经中国作协办公室介绍,丁玲出院后,已搬到友谊宾馆暂住。我马上打电话到他们住的房间,是丁玲先生接电话,让我4月20日下午去她的住处。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我约了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秉元一道前去访问。在友谊宾馆东北区7217房间,我第一次见到丁玲先生。陈明先生开玩笑说,“老丁,你们安福县(临澧旧称)人真有办法,刚搬家嘛,这么快就找到了我们”。那天,丁玲先生不仅热情地为我们回忆了林老在保安和延安的一些往事,谈到林老给予过她的关怀,还为我们谈到毛主席、周总理,谈到彭老总、向警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面对老人的侃侃而谈,我作为她家乡的文学后辈,没有感到丝毫拘谨。她那天所谈,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予以记叙。倏忽之间,时间虽已过去近30年了,丁玲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那么强烈——特别是她那双深邃而明亮的大眼,她的案头的一毛钱一支的竹杆圆珠笔!尽管岁月的年轮爬满她的额头,在一位久历磨难、已是75岁高龄的老太太身上,却读不出半点哀怨和颓唐;她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对社会上刚刚冒头的一些不正之风,又时而露出隐忧并予鞭挞。不能不使人感到,无论是北国边陲的风刀霜剑,还是秦城监狱的铁窗生涯,都没有销蚀掉她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湖湘文化赋予这位文学前辈的率真和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