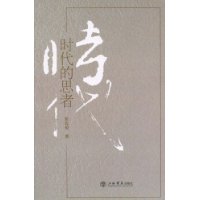时代的思者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时代的思者 |
 |
|
 |
时代的思者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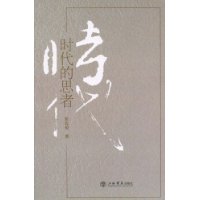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页码:16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
·ISBN:7545801245/9787545801248
·条形码:9787545801248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时代的思者》内容简介:哲学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智力,更考验一个人的心力。心力比智力更重要。聪明人不一定能当哲学家;哲学家不一定聪明。每一个时代都不乏聪明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
作者简介 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国在宾州州立大学作博士后,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作访问学者。1992年秋回国工作。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5年升为正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主要著作有:《激情的事想》(1998年),《坚持理想》(1996年),《历史与实践》(1995年),《张汝伦集》(1991年),《意义的探究》(1986年)及近百篇论文。
编辑推荐 《时代的思者》:继《中西哲学十五章》之后,复旦哲学系著名教授张汝伦又推出新作《时代的思者》,与前者不同的是,这本新书是张教授的散文集,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融于充满哲学意味的文字之中,一定能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目录 国学与当代世界
现代中国哲学之身份认同和自我批判——以熊十力为个案的研究
再论人文精神
我国人文教育的现状及其出路
拨地苍松有远声——读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和《九十年代日记》
大学之道和现代大学教育的缺失——我读《大学一解》
极权主义的病理诊断书
永远的康德
海德格尔与大学改革——纪念海德格尔逝世三十周年
真实感受世界——悼苏珊·桑塔格
海王星人如是说
霍布斯鲍姆:清醒的理想主义者还是顽固的浪漫主义者?
遥想全老当年
桃李不言自成蹊——悼王玖兴师
哲人不死——追念金克木教授
时代的思者——敬悼王元化先生
艺术中的哲学
……
序言 问:您的德国哲学研究一直为国内学界所称道,但您近几年来似乎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讲授之中,请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哲学研究上的转向?除了个人兴趣的变化之外,这种转向是否有哲学上的原因?
答:这不是哲学研究上的转向,更不是个人兴趣的变化。我向来不认同将哲学条块分割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所谓二级学科,然后每个人选一个“专业”来从事。这不是哲学的方式,更不是哲学,而是专业技术的方式。但哲学毕竟不是技术,而是思想。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流动的、相通的。没有什么比让思想停留在一个人为划定的圈子里反复操练更可笑的事了。现代这种按“专业划分”的所谓哲学研究,只能出哲学专家或哲学教授,而不能出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如果说要有专业的话,那么他/她的专业只有一个,这就是思想本身。不管是什么传统背景的哲学,都是他/她思考的养料与对象。而人类的哲学史已经表明,不同哲学传统的融合会大大推动哲学本身的发展。
至于我本人,就像我在《德国哲学十论》的自序中写的那样,从来没有想当德国哲学的研究专家。最初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只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希望现代中国文化和思想能重现古代的辉煌。王国维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
文摘 望认同自身的过程。正是随着全球化过程的进行,这些群体产生了要在全球一人类环境的关系中认同自身的愿望。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又保持其认同感。当闻一多写下:“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这些灼热的诗行时,他是用诗的语言写下了中国人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认同焦虑。
这认同焦虑是这波国学热的内在原因。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承认普世价值,也不能代替文化认同。现代性并未给予人类以明确的方向,它充其量提供无方向的方向——追逐眼前利益。文化认同并不是刻意突出自己的文化特性,而是在自己身历现代性危机之后,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要向何处去。正因为未来没有预定的方向,我们才迫不得已从自己的过去中寻找给自己未来定位的坐标。毕竟路要自己走,认同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坐标,找方向,找立足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作为传统思想的结晶,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是自然的。
尽管如此,国学仍然面对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它的种种质疑。首先就是国学乃专制之学,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非彻底抛弃不可。由于百余年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发展缓慢,国学更是常常成为替罪的羔羊。“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为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①谭嗣同的这段话代表了许多人对国学的看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似乎成了不刊之论,实际上却是偏激之论。国学中当然包含有专制色彩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反专制的东西。当初国粹派就提出要区分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君学与国学。焚书坑儒之类的惨祸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从反面说明传统学术思想必有与专制主义格格不入之处。用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称国学本身是近代最大的学术偏见。
虽然前人已经提出要区分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君学与国学,但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