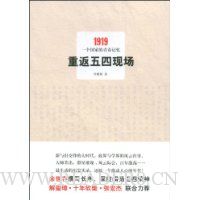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页码:32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 ·ISBN:9787505725225 ·条形码:978750572522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
 |
|
 |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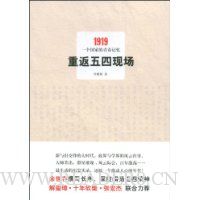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页码:32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
·ISBN:9787505725225
·条形码:978750572522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图书品牌:北京磨铁文化
内容简介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是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们高揭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了街头,宣告回归革命时代。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也终于纳入了河道。
五四时代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时代。它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有人把它称为文学革命运动,有人把它称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把它称为启蒙运动。
作者简介 叶曙明,广东作家。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军阀》、《草莽中国》、《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共和将军》、《大国的迷失》、《广州旧事》、《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雕刻美色:广东玉雕》、《大都市综合症》、《女巫之歌》等十几部著作。
媒体推荐 感受那代书生的青春激情
——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十年砍柴
我和叶曙明从未谋面,谈不上熟悉。但我知道,《重返五四现场》是他种因久远、打磨多年的一本著作。
今年2月底,我去海南参加天涯社区十周年庆典,旧雨新朋会聚三亚,闲谈中说起了当年天涯社区特别是我当年常去流连、受惠非浅的关天茶舍板块。大约2002年左右,关天茶舍聚集了一帮很有见识的读书人,那些ID当初刚出江湖,后来名满网路,而现在,很少在关天茶舍露面了。比如易大旗、童天一、王怡、冉云飞等,其中还有ID为“一听”的叶曙明先生。当时他正致力于研究后世争议颇多的陈炯明,以及广东地区的“红卫兵”历史,这两件事或远或近,和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乃至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2年5月2日,叶曙明在“关天茶舍”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又来了 照例纪念一番》的文章,《重返五四现场》的主旨已现于这篇短文中。
叶先生在那篇短文中开宗明义便道:“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一旦失去皇权的靠山,便再没有了往日的威摄力。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的一课,那么,它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为新的政治权威作诠释的使命。这就游离了《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的初衷,也是导致新文化运动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文化的巨匠们,几乎无一不是怀着急切的救世之心,他们引进西方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 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陈独秀就曾幻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样一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最终被升格为‘德菩萨’和‘赛菩萨’,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今距叶先生写那篇帖子7年了,7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一瞬,但在网路中却像一个世纪漫长,其间中国的网络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世界已经完成了彻底的社会化,不再属于少数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士之乐园。叶曙明先生当初那篇文章中所埋下的因,经七载寒往暑来,终于开花结果,有了这本煌煌30万字的大作。
五四距今90周年了,身经其事的一堂师友,都已先后作古了。五四运动,在后世官方的言说体系中,经过一番拨弄,早就成为一个“符号”,套用叶曙明形容科学民主升格为“德菩萨”、“赛菩萨”,“五四运动”早就被赋予神格,高居太庙之上,供人顶礼膜拜。而一个人或一件事,一旦神化,基本上会遮蔽其本来面目。《重返五四现场》,就是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当然,事隔九十年,后人说史,容易陷入“罗生门”之争论,没谁敢说自己所说的就是百分百的真相,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抱以一种公允的的态度,尽量摈弃各种因意识形态而先入为主的成见,用史料来说话,如果能这样做,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重返现场,最重要的是要去掉“五四”那代师友日后分道扬镳,所获得不同的官方评价。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卷入了后来的政治纷争中,成为对垒双方的重量级人物。但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是朋友,是同道者,尽管彼此在性格气质和观点上不无差异。重返现场,就要去掉日后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庙堂的褒贬谥法,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这是我对叶曙明“重返”的理解。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一点今天看来应无疑问。那一代读书人在青葱年华的激情和行为,影响了尔后的九十年,这种影响还在延续。除当时已有江湖地位的师辈,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那些五四的孩子们,当时多是热血青年,读罢叶曙明这本书,似乎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国难当头时一代书生的青春躁动。他们在喧闹中高扬了爱国主义的大旗,这面大旗过于堂皇高大,遮住了大树下面那些丰富的物种,其实就在赵家楼烧起大火的那个夏天,被外界视为愤怒青年的他们,所持的态度并不一样,有些人差别很大。只是这代五四之子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后人对他们当时的行为,容易产生一种整齐划一的印象。他们当时的差异,决定着他们在这场大戏谢幕后的人生选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张国焘,也包括五四前已离开北大,南归湖湘的毛泽东。这种态度差异决定人生差异也在他们的师辈身上应验,如陈独秀和胡适。
后世写史者,最大的诱惑,也可说是痛苦,总是不由得设身处地把自己放置到历史场景之中,替古人担忧,替后人惋惜,明明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却忍不住设计一条条无法证明的历史路径。就这样,前辈人的血泪情感,一点点催白了写史者的双鬓。
历史现场早被破坏,流失岁月永不再来。但我们总想重返,不为好奇,只希望重返的努力,或许有益于未来的路径选择。
编辑推荐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你将领略新与旧交锋的大时代,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大师辈出,群星璀璨,风云际会,百年激荡……
最生动的历史实录,还原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余世存撰写长序,深度阐扬五四精神
解玺璋·十年砍柴·张宏杰联合力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锷、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陈炯明、章士钊、傅增湘、吴稚晖、张东荪、鲁迅……时势造就英雄,人才成就时代。
五四时代的北大,群星璀璨,出入的都是当世名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顾颉刚、马叙伦、刘文典、马其昶、梁漱溟……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有请大师们重返五四现场!
专业书评 叶曙明是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
——台湾大学教授 蔡源煌
叶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现场》一书让我们跟着他重温了五四……以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作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著名学者、作家 余世存
长久以来,五四被各种思想搞得面目全非、奇形怪状。现在,我们跟随作者,穿过重重迷雾,重返五四现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五四的真相,这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出版人、评论家 解玺璋
叶先生这本书是认真的、有才华、有见解的信史,为我们细腻而有条理地梳理呈现了民国史上重要的一个片断,它不但扩充了我们对民国史的了解,也为我们反观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个角度。
——新锐历史作家 张宏杰
《重返五四现场》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著名专栏作家 十年砍柴
目录 序:百年淬厉电光开
上篇 启蒙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 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人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六章 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记
……
序言 百年淬厉电光开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序
余 世 存
一
五四运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这个由蔡陈胡鲁们引导、由傅罗段等人发动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经由国共双方以及胡适、罗家伦、毛泽东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巨人们的评估,已经被定性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者。即使反对五四运动的论断,也承认五四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五四运动撕裂了文明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
但五四运动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的当是时究竟是什么状态,至今人言言殊。当时参与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是否如同当下的网络中国,有着混乱的自由?当时人以及当下人是否都善用了这种自由?当时人和当下人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资源、道义支撑?不仅如此,关于五四运动的全部言说仍归属两大阵营:赞成,反对。即使“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伪命题滋养当代知识界十年之久,赞成者仍难在复述旧言外有新说辞;而反对者或嗫嚅其言或冷嘲热讽,甚至从“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中将百年中国的罪苦归结到五四运动。
近百年前的一场运动至今仍给我们情感的波动、认知的分野。这说明我们确实在心智、视野、群己权界、历史观念、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运动的阴影;我们在革命、改良、文化、运动等方面仍未有历史的共识或伦理共识。据说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为古物、即属历史,即可成为公共财产供全民保护、认知、怀古。我在大众游玩的地方,也确实见过墨索里尼的遗迹,独裁者当年演讲的阳台;我见过对垒牺牲的两军将士的墓园,那样分明又统一地成为今人的历史风景,一种意味深长的厚重之美。但我们的五四,无论赞美或反对者其实都尘封了它,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阵营归属而未能展现其全部的真实,未能成为人民当下生活的真正背景。
二
康梁孙黄的革命,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长达百年的启蒙、理论准备。顾、王、黄等人的担当,曹雪芹、龚自珍们的天才创作,仍只是挽歌而已。徐继畲、魏源等人的思考,也不足以给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故曾左李摸着石头办洋务,康梁黑猫白猫地借孔改制变法,孙黄自备学说或建国大纲,政道合一,酿成“不彻底的”辛亥革命。
蔡陈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本是补辛亥革命的思想道义之缺失,在政统崩解重构之际,别立可审判、监督、分权的道统。但运动的领袖们虽然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尊奉德赛二先生,他们并未能像启蒙运动中的西人那样获得人的自觉而沟通人心,也未能像百科全书派那样为华夏或人类的一切领域立言立法。
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圣贤有失公允。何况当时的中国确实内忧外患,亡国亡种之说夸张,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中国实为木乃伊般的国度。以胡适之温和,到抗日战争,才说中国终于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演变成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同情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背书。它支持了政治革命、全民革命;但它还没有承认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它失望于政统的混乱,但它未能夯实并强调道统,它未能如周作人说的努力经营“自己的园地”,反而介入并为政统的变革所裹挟。
如果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将如何演变?孙文学说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理论,但他有建立道统的用心,袁世凯复辟也是敏感到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欲寻求道统的支撑,因此,南北军阀的割据和兼并不会比五代十国更糟,反而会在思想资源上争胜。显然,中国仍会在世界的带动下进入革命的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少有从道统的角度梳理革命,多将现成的革命介绍给政统以充任思想争胜的奴仆、苦力。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们知行合一,成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加快了这一革命进程。“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更彻底的革命抛开。革命发生了变异,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登场,到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
……
文摘 五月四日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
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
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北大学生方豪说:“于1919年的5月4日上午8时,在北京的天安门前聚集了一万左右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方豪《回忆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金华(市)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版。俞劲也说:“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约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许德珩的回忆录是这么写的:“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三千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但更多的回忆材料都说,天安门前的示威活动,是从下午才开始。上午9时,各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下午的游行路线,决定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以表达愤怒。傅斯年被推举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由他正式宣布,下午1时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前往东交民巷进行和平的示威抗议。
但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团体,傅斯年并不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已下了决心,必要时以暴力进行抗议。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蔡氏神色凝重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他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
……
后记 后记:1919年3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笔,因为那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北大会议,决定让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在多年以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其实,胡适有点自欺欺人。陈独秀即使不离开北大,也不会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因为陈独秀思想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无论是打孔家店也罢,白话文运动也罢,与林纾论战也罢,他都站稳了一元绝对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宣称《新青年》的主张不容匡正,不仅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归宿,而且也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路向。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吸收俄国革命养分成长起来的,和自由主义完全不搭边。由江湖会党为骨干的同盟会领导,以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由主义化。所以,胡适大可不必感叹。李大钊没离开北大,他不也一样信仰了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新文化运动同样不会使中国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因为它的性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一课,这决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绝对姿态出现。虽然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桂冠赠予了它,但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文化基因、思想谱系,还是前因后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DNA,无法相提并论。
所谓启蒙运动,是要启自由与理性之蒙,但什么是自由与理性?只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学说统统纳入这场运动中,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局面,才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理性的苏醒。但回顾历史,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出现,随着国民革命的勃兴,国民党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方向演变,最后甚至出现了“革命的进此门,不革命的滚出去”、“不为同志,即为叛逆”的极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胡适就曾感叹,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其实,这同样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肇远因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承近因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前驱,以救亡为己任的。所以,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盘桓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在民族主义的基因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启了革命之蒙,启了救亡之蒙,并不存在“让位”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干扰”。
但如果说它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也不对。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新旧对抗,而五四运动是朝野的政治博弈,范畴不同。用“五四时代”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二者,但用“五四运动”,则容易产生歧义,不足以涵盖二者。
在这一个舞台上,在这一出戏里,只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哪个是红脸,哪个是黑脸。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也有来自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孔家店的发源地,决不容日本人侵占;保卫山东就等于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样。
这实在太吊诡了,以至于常被左右为难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运动打了半天孔家店,但当民族危机发生时,孔家店却依然是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还能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吗?或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吗?当初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对立面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谓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历史的因果丝毫不爽。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环紧扣一环,这是一个必然的、连绵不绝的过程。因此,胡适的感叹,如果扩大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皆起于新文化运动之会”,并承认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历史盛会的推手之一,就与事实相距不远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当我想把这段历史再梳理一遍时,已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讲述了,只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读那些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
对中国的历史,也许我有过于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么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历史确实被某些事件改变,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被改变的东西,才属于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这种宿命感,把我的这本书,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与著述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
2009年2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