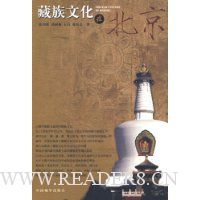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 ·页码:251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3月 ·ISBN:9787800579974 ·条形码:978780057997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藏族文化在北京 |
 |
|
 |
藏族文化在北京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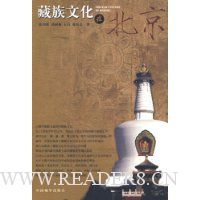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
·页码:251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3月
·ISBN:9787800579974
·条形码:978780057997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藏族文化在北京》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该书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调查,研究藏族文化在北京传播的历史,及其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影响。该书主要内容共分11部分,另加附录。一、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1247年,萨迦派高僧萨班携侄儿八思巴等赴凉州,代表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与蒙古王阔端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西藏地方正式归顺蒙古汗国。萨班圆寂后,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教主,并与夺得蒙古汗国大汗、后成为元朝开国皇帝的忽必烈政治结缘,被封为帝师。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北京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发展而地位不断提高。至元九年(1272年)定为国都,称为“大都”,由金朝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金中都),上升为国家京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帝师和一大批喇嘛僧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
由于历史原因,藏族关于政治、历史、自然、文学、绘画、医药、科技等知识,都汇集于宗教,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喇嘛教是藏族文化的载体,喇嘛是藏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元朝崇奉喇嘛教,封赠八思巴和萨迦派的历任教主为帝师。同时,设置宣政院,掌管吐蕃及全国佛教事务,而以帝师领其事。元朝共封十余名帝师,他们带领大批徒众(包括维吾尔及其他各族皈依喇嘛教的僧人),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
三、建立喇嘛庙,把藏族文化写在了大都的蓝天。
编辑推荐 《藏族文化在北京》: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
在13世纪中叶的元代,从远在万里之外的西藏传播到北京
清代以汉、满、蒙、藏、维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象征,空前地提高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辉煌壮观的藏传佛教寺庙和佛塔等藏式建筑,以动人心弦的建筑形象,将藏族文化永久地刻写在北京的蓝天下,对于古都个性特点的形成和皇家园林性格的塑造,都有着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藏族文化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目录 前言
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
帝师和一大批藏族僧人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
建立藏传佛教寺庙,把藏族文化写在了大都的蓝天
皇家“做好事”,藏族文化笼罩在香烟缭绕中
藏族文化在元大都结硕果,中国文化史上添奇葩——蒙古国子学和藏汉文大藏经对勘
明清两代崇奉藏传佛教,一大批藏族喇嘛长驻北京
明清两代遍布京城的藏传佛教寺庙
大、小金川一批藏族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
藏族文化为皇家园林添彩
故宫秘藏的藏族文化
藏族文化融人老北京的社会风俗中
附录 民国初期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
序言 “藏族文化在北京”——如果作为谈天说地的话题,许多人(包括很多“老北京”在内)都会感到陌生,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它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这是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可以用八个字略加概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多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这是由于北京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北京地处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大平原结合部的战略要地,明朝人称它:“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沧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①其北接蒙古高原,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北京猿人”所代表的中华古老文明的曙光,琉璃河周文化遗址、大葆台汉墓等所展现的商周秦汉灿烂文化,都会令人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渊源、血脉浮想联翩、遐思无限。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的山戎、奚、库莫奚、靺鞨、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都和广大汉族一起,在这一带留下了文明进步的足迹(长城就是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和交流的遗迹),因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兼容并存的区域文化特色。
文摘 插图:

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
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
13世纪的中期,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元世祖忽必烈制订、推行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大批藏族高僧由西藏高原来到京城,于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但是,要具体说明这个问题,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做长期的、艰苦的考察、研究。为此,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透过沉沉漫漫、迷雾笼罩的时间隧道,揭示那历史的一页又一页,并将它展示给读者。
一、元大都的建立
公元l206年,在中国漠北草原的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发生的一件大事,永远“定格”在历史老人的记忆中——因为它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了,但是借助于历史科学的抽象力,我们仍然可以想象那壮观的一幕:在“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广阔草原上,万骑云集、人头攒动,迎风猎猎的九斿白旗,在蓝天白云下格外引人注目。在这蒙古各部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上,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国大汗,号“成吉思汗”。刀矛马鞭齐举,遮天蔽日;欢呼呐喊,震山动地。这似乎是宣告天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大元”王朝即将来临。
成吉思汗胸怀大志,谋勇兼备,史家有“深沉大略,用兵如神”之誉。他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经过2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又攻金灭夏,西征中亚,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被尊为太祖。
后记 2002年7月,我和刘丽楣、王红两位副研究馆员组成课题组,接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的《藏族文化在北京》研究项目,除了感谢他们的信任外,心里也感到有些惴惴不安,担心限于能力和水平,不能按期交出合格的答卷。好在我们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又有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今天终于可以为这项研究成果画上一个比较满意的句号了,心里油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三历寒暑,一千多天的灯下爬格子之苦,总算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以后的事情,就是洗耳恭听读者的评论。至于打分多少,暂且不顾,以后我们还要不断修改。
这项课题能够如期完成,首先应该归功于刘丽楣、王红两位副研究馆员从课题设计、研究计划的制订,以至于查找资料、实地调查和部分章节的撰写等付出的大量劳动。张双志也提供了部分史料,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我们还多次共同讨论研究,拟订了编写提纲,由我负责全书的审定,作为课题组的共同研究成果分送有关专家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