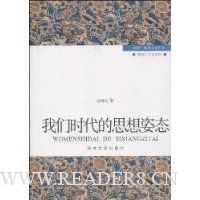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页码:28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 ·ISBN:7560841155/9787560841151 ·条形码:9787560841151 ·版本:第1版 ·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 |
 |
|
 |
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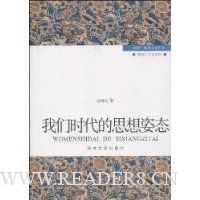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页码:28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
·ISBN:7560841155/9787560841151
·条形码:978756084115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同济·欧洲文化丛书,德意志文化系列
内容简介 《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内容简介: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已,虽然这一种思想方式在后哲学时代里仍旧起着主导性作用。所谓“后哲学”仅仅意味着除哲学之外其他思想方式的可能性。后哲学的思想将会有一个更为自由开阔的课题范围,因为它面临着一个没有边界的多元文化世界。在这个由于技术工业的普遍作用而导致文化全面失度和失控的时代里,思想正在经受咄咄逼人的考验。
《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收集了作者20世纪90年代的短篇作品,凡二十四篇,记录了作者主要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出发,对西方哲学传统、当代哲学文化、现代技术、诗-思关系、东西方哲思差异等课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 孙周兴,男,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理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浙江大学教授;1999年至2001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Wuppertal大学从事访问研究;2002年4月起任同济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等。
主要从事欧洲大陆哲学研究,尤以德国哲学和现象学为重点。著有《说不可说之神秘》(1994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2001年)等;编有《海德格尔选集》等;译有《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林中路》、《路标》、《尼采》、《权力意志》等多种。
编辑推荐 《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同济·欧洲文化丛书,德意志文化系列
目录 自序
第一编 哲学与时代
在何种意义上讲哲学是西方的?
什么是科学?
技术和新人类图景
不朽的反讽
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普遍交往时代的交往哲学
我们时代的理论姿态
失去边界的哲学
第二编 诗歌与思想
存在历史的转向与语言论转向
诗的源始
启蒙的界限
在思想的林中路上
译读海德格尔的一组诗
神圣者的踪迹和思想的虔诚
奥斯维辛之后思想的责任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
第三编 东方与西方
道·道说·道路
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
我们如何敲打词语?
后期海德格尔基本词语的汉译
亲在的境界
玄妙之门
思想的本色
这个人在世纪末的仓皇
再版后记
……
序言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欧洲文化丛书”之“德意志文化系列”,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文摘 我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进了杭州城。我在中学里没有学过外语,连26个英语字母都念不周全,高考时在可以打勾的地方胡乱打勾,竟也懵对了15分——我的运气据说在中偏上(好在当年外语只计百分之三十的分数)。到了大学里,我仍旧十分真诚地想:好端端一个中国人,学什么鸟外语呢?我被安排在英语低级班里,从ABC开始学。有一次英语老师让我念一段课文,我咕噜了一阵,好像在讲绍兴话,没有人听懂,只赢得了满堂的哄笑;以后这位老师再没有让我念过课文,倒也让我清闲着。对于地质学专业,我进校不久就失去了兴味,于是常常逃课,自己躲起来看看小说诗歌之类,竟也写了一些酸溜溜的诗。
这里顺便插一段。我从自己的经历里得出一点:我们的大学制度是必须彻底改革的,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教师开什么课,教授什么,学生选什么专业,学习什么,都必须是完全自由开放的。若没有这两种自由,大学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就意味着劳命伤财。想当年我们一个班共27位学生,现在仍在从事专业工作的只有二三人!这是什么样的培养效果?!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度完了大学生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泰山脚下的一个矿业学院教书,教的是“普遍地质学”和“大地构造”两课。以我在大学里的学业情况,这时自然免不了误人子弟了。其时生活沉闷,心灵开始发育,就对哲学生出了一点兴趣。到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发狠地自学德语。
工作第三年(1987年),我报考了母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后记 如果从1990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诗的源始》算起,我写字、治学的经历也近20年了。近20年里,我的主要业务却是学术翻译。或有空闲时,也写些短小的文章,多半是一些读后感或者译后感之类,无足挂齿,不过好歹也算是本人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点心得体会。到2000年时,经学兄倪梁康教授安排,我有机会把十年的短章集成一册,就是眼下这本小书了。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农村,老家位于绍兴南部山区,离城约有40公里路程。虽然旧时绍兴乡间一直有“耕读之家”的风俗传承,但经过“文化革命”的动乱,淳朴民风丧失殆尽,人心不古,只把心思里的恶俗和野蛮挑动了起来,哪里还会有什么书卷之气可言?因此,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我小时候少有机会读书,也根本无书可读。高中毕业那一年我才读到了《红楼梦》节本,而此前几乎连接触期刊的机会也没有过。外文就更不用说了,高中毕业时我还没有把26个英文字母认个完全。这些悲哀的故事,恐怕现在的后生们是无法设想和体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