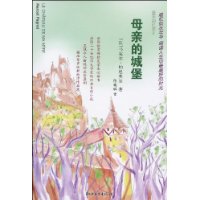|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母亲的城堡 |
 |
|
 |
母亲的城堡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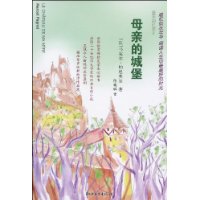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页码:202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
·ISBN:7533928814/9787533928810
·条形码:9787533928810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童年回忆录
内容简介 《母亲的城堡》是对一个失去的年代的风证,一首小小的抒发孝心的歌曲。法国教育部指定学生必读书,法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自传小说,呈现令人愉悦的成长喜剧,描画罗旺斯的诗情画意。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何况他也不是本书的主角,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证人.
作者简介 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1895-197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电影上的成就,受到电影大师罗塞里尼等人的推崇。帕尼奥尔擅长描写法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普罗旺斯的诗情画意和对家庭的眷念之情。六十岁后发表的总题为“童年回忆录”的自传体小说,以幽默逗趣的笔调叙述小马塞尔的童年生活和少年时光,为他赢得文学上的巨大声誉。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法国教育部指定的学生必读书。
译者简介:
陈曦琳,自由译者,译作有《拿破仑情史》、《只要在一起》等。
媒体推荐 法国青少年在书中认识的第一个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帕尼奥尔笔下漫游在普罗旺斯山区的小马塞尔。
——法国《费加罗杂志》
如果想到斯蒂文森、马克·吐温和高尔基,我发觉在帕尼奥尔以前法国文学完全不能描写一个儿童发现世界时那种特有的、既紧张又兴奋的迷人经历。
——著名小说家、学者: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
帕尼奥尔是一个极会卖弄关子的说书人。他友善的笑容里透着几分狡黠聪慧,就像阿尔封斯·都德一样,在普罗旺斯灿烂的阳光下溅射出耀眼夺目的才华。
——法国《文学文献》
马塞尔·帕尼奥尔是第一位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电影工作者。他的作品吸引人,是因为除了自然且略带戏谑的语调外,亦流露出一种对过去岁月的淡淡哀愁。
——法国《夏朗德自由报》
这书太可爱了,翻译它是一种享受。到最后一次存盘时,当然也伴随着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终于可以阶段性地把显示屏和键盘这两件假设从身上卸下来。可又多么失落,从心底莹,我是巴不得每天去那岭子里消磨我的时光的。
——本书译者:陈曦琳
编辑推荐 《母亲的城堡》:
追忆似水年华,阅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序言 如果不算几次不起眼的尝试,这是我第一次写散文。
我确实以为有三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用于歌唱的诗歌.用说话体现的戏剧,以及用书写表达的散文。
令我害怕的,不是选择词语或者表达方式,也不是语法的精微之处——说到底,这一切大家都能掌握——而是小说家的立场,更加危险的是回忆录作者的立场。
讲自己很难:作者谈到自己的全部缺点,我们都乐于相信:而他谈到自己的全部优点,我们必须有了证据才接受.我们还遗憾他没有把好话留给别人代他说。
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何况他也不是本书的主角,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证人.
文摘 可歌可泣的大王山鹑事件后,我一下子进入了猎手的行列,不过扮演的角色是猎物撵手和拾回猎物的狗。
每天清晨四点左右,父亲推开我卧室的门,悄声道:“你来吗?”
无论于勒姨夫的大鼾,还是皮埃尔表弟半夜两点讨奶的啼哭,都不足以穿透我的睡眠,可父亲悄悄儿的一声就能让我蹦下床来。
为了不惊醒我们的小保尔,我摸黑无声地穿好衣服,然后下楼来到厨房,于勒姨夫眼睛肿肿的,带着大人醒来时有点发愣的样子热起了咖啡,父亲装好猎袋,我往子弹带里填满子弹。
我们蹑手蹑脚地离开。于勒姨夫锁好门,绕过去推开厨房护窗板,把钥匙搁上窗台。黎明是凉爽的。受惊的星斗眨着眼,白惨惨的。鹰坪的岩坝上方,变得单薄的夜幕镶着白雾的花边,小眼山的松林里,一头忧郁的猫头鹰正向星星们道别。
我们一路顺着曙光登山,一直到“雷都诺”的红岩,但我们一声不吭地闪了过去。因为弗朗索瓦的儿子巴蒂斯丹在那儿踩过点,替他“蹲点”弄雪鸦的利器是小棍加黏胶:搞得他常常连头发上也缠着胶沫。
我们在山影子里纵列行进,接着到了巴蒂斯特羊舍。这是一处古老的羊棚,我们的朋友弗朗索瓦和他那些山羊有时会在里边过夜:就在这地方,绵延向陶美峰的平原上。旭日的红色光芒一点一点地现出了松树、刺桧、荆豆,仿佛巨舰破雾而出,孤峰如高高的舰首蓦地挺立在我们面前。
猎人下到山谷,一会儿折向左边的爱斯古普莱斯峰,一会儿拐进右边的细驿谷和帕斯当。
我在坡台上走,离开岩坝不超过三四十米。我把一切扑腾的玩意往他们那儿赶,要是碰到了兔子,我就往峰顶方向跑,大幅度比画信号,像从前的水手那样,于是他们赶忙上山找到我,一起对那长耳生灵展开无情的围剿。
我们再没遇到过大王山鹑,没有,一只都没了。不过我们不说,还到处找,尤其不放过那条沟壑——我们建功立业的圣地……我们贴着地面,在胭脂虫栎和绒岩蔷薇底下爬到沟边,常能从里面引出山鹑、野兔,甚至还有一头獾——被于勒姨夫在险些超出射程的地方放倒:可是大王山鹑飞进了传奇,从此便守着传奇:肯定是怕了约瑟夫了,光环把约瑟夫衬得魁梧了。
荣耀加身让他有了震慑力:成功往往造就天才。相信往后自己的“国王绝招”将弹无虚发,他果然变得百发百中,还分外地气定神闲,于勒姨夫终于禁不住感叹道:
“这可不叫‘国王绝招’了,这叫‘约瑟夫之射’!”
不过于勒姨夫照样是无与伦比的,所有夺路而逃的兔子、山鹑和乌鸫,他能“屁股朝前地放枪”(用他自己的话讲),
……
后记 我更愿意在这里留下两整页的空白。不是有意搪塞编辑朋友,是作为一种表达。
你们知道,不是每本译著都必须包含一篇译后记的。那么是不是一部以译后记作结的译文意味着,或者说更接近于某种完整呢?关于这个问题已无须深思。仿佛一盏终年运转不息的探照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千古名句自动地将它有力的角度切入我们每一次对完整与否的考究。不止是完整之辨,也是主客观之辨。而在我此刻看来,它其实不是要立一个论断,更多的是在面对“真面目”的难辨和不可求时,油然而来的浩叹。
推论下来,译后记之于译者。竟是一项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