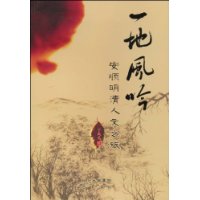|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一地风吟:安顺明清人文之旅 |
 |
|
 |
一地风吟:安顺明清人文之旅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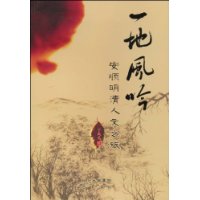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页码:362 页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ISBN:7807522380/9787807522386
·条形码:978780752238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一地风吟(安顺明清人文之旅)》内容分为四个版块,以人系事,回溯追忆明清时期安顺人士和来安顺的人士的行迹言行。“人文”则是三十三篇非虚构性文化散文赖以串联的红线。不论今人古人、天子庶民,也不过以天地为羁旅,百年光阴,倏忽而过。然而人文不灭,文采风流,世代芬芳。正是作者刻意关注人文,着意描述人心,抒情写意,皆成锦绣。
目录 春风恨不到天涯(代序)
壹 岁月留痕
兴学记
征服者
卫所的建立与卫学
尚存的历史印记《郭子章疏》
康熙朝:一个文教蔚兴的年代
“文教遐宣”匾与安顺义学
科举之路
习安书院的创立
历史风云中的凤仪书院
短暂的学堂时代
瞿鸿锡与安顺中学堂
驿站烟雨
160知府600县官
沉重的翅膀
罂粟花开时
贰 长路心语
徐霞客过安顺
天涯孤旅
行陌路
戊寅年四月十九日
安顺:二十八个字
异境天开
面揖飞流
唤醒山灵
大山之缘
远去的背影
梅月双清
智者厂石
1746年之后的陈法陈庆升父子
遥远的绝响
杨树做官的二十个“不为”
梦归何处
满天是凌云
蹚过混浊的河流
叁 风雨人生
进士第一人
梅豸之仁
徜徉于天堂地狱之间——悲情吴三桂
千叟宴上一奇翁
父子两清官
胡林翼的牛刀小试
奇人杨春发
砚石山农
何威凤的传奇人生
亮太阳
人间情
入泮路
青云志
京华行
行路难
凤之仪之寄语青鸾
凤之仪之振羽丹山
肆 屯堡一束
鸟鸡龙藏与安顺屯堡人
最早的屯堡
唯忠为大的标记“待诏亭”
神佑
云山遐想
青山遮不住(代跋)
后记
……
序言 春冈恨不到天涯
安顺是个什么地方?旧志承上称其为“黔之腹,滇之喉”,听上去还有点通衢要冲的意思。然而数十年前我从黔中腹地来到川西天府求学谋生,早些年每有学兄同僚问起籍望之类,我甫应诺,人家每日:呵,安顺场么!这真让人气短。安顺旧称府,现代好歹也是个地级市;而安顺场乃四川石棉县的一渡口,古今都是乡镇建置。不过七十多年前,工农红军长征中由此越大渡河;又七十多年前,洪天王麾下翼王石达开在此丧师殒命。说到底,地名之有名,全靠有大人物上演出大事件。从字面说,南华智者庄生所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强调个人感受;就大处言,安天下,顺人心,社会安定,生计顺遂,于国于民,“安顺”二字作为地名,绝对是汉文字文化中的上品之选。
我等便是安顺人,是非土著则毋庸讨论。我们生长于斯,父辈的灵魂已安息在这里的山水之间,这便是家乡,斯地即为根。但也没有自豪的理由,多少年来,外地人——京沪湖广不说,即在省城贵阳以外的人们眼中,安顺人?不过是一群来自蛮荒之地的乡巴佬。长年在外谋生干事的游子心里明白,别人有权这么看。倘若你是我们这一帮,生于新旧交替的上世纪50年代,而对此“俗眼”,先前会有些愤愤然,尔后也会心平气和。你明白,和皇城京都、十里洋场,乃至天府之国比起祖先的史上辉煌,差远了,不是一个级别。但这些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讨论我们自己:生于50前后的安顺人,幸耶,不幸?
显而易见,这一段风云诡谲,世道艰险。涉世之初,我们便饱尝苦难、野蛮、凶险,也曾颠沛流离,长歌当哭,但这只是一个层面。更多地,我们昂扬奋发,勤奋磨砺,求索真理,拥抱美善,播种良知;更重要的,我们将苦难据为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还拥有一个盛满人间悲喜剧的称谓:老三届知青。早先有一部知青小说名《蹉跎岁月》,我一直不以为然,为何不叫“峥嵘岁月”?知青下乡的利弊,兹事体大,姑且不去讨论。它或许荒废了一代人的学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但仅就对这代人人生抱负、意志品质的磨炼,日后肯定是难觅此良机了。我们的下一代,80后的年轻朋友,就谋事交友,气量毅力,也即生存能力方面,恐怕和我们“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
许多基本的生存技能,今天及以后(尤其是城镇中)的年轻人不会再有机会实践——如我者,干过水田旱地里的所有农活,梭爬过千米深的土煤窑,吆过马车推过鸡公车,也曾开山放炮修铁路砌砖墙石墙作木工钳工,会祭神退鬼撰碑联写神榜,能焐豆豉也会酿甜酒烤烧酒,会种茶炒茶品茶,也能养鸡放鸭杀猪置办酒席,也抽烟喝酒娶妻养子,与此同时也能读书抄书偷书教书写书——这在我们这一代,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一小群安顺兄弟中不过是平常的生活经历、生存方式而已。——1973年冬,我在安顺边陲一个叫高寨的小村做民办教师,用十来天时间,将此前五年的几十本读书笔记中的文史哲译作部分按主题选编成十类,整理出十几万字的格言录,抄满了一个小32开的厚笔记本。到了1984年中秋我已在川西负笈求学,是夜星月朦胧,我在笔记本后扉页写道:
如今这种名人格言集已比比皆是。然而它可贵之处是辑录在十一年前,那是文苑中百花凋零的年代。
那时候,我和朋友们几乎不能糊口,而寻书等于盗宝。借、求、诓、高价买,乃至做梁上君子。一页、一卷、一部搜了来;马上、车上、路上、枕边,煤油灯下,柴火光里;读、背诵、抄写、畅读,才辑出了这本小格言录。其勇可贾,其志可嘉;难能,不易啊。
不希望下一代遭此乱离,却希望他们有这点志气,这点毅力。
不幸一语成谶。现实让人揪心,我们的下一代聪慧阳光,活得实际、实惠、实用。不知多少人还有梦想、理想、信仰?相信人间还有永恒的事物?仰望头顶的星空,顶礼膜拜?遭逢天地间的大悲愤,大感慨,还会不会鼻梁发酸,心尖刺痛?
几十年来,我也曾将这些疑问反复拷问我们自己。结论始终如一:我们有。我们会。我们一直在这么做。
文摘 插图:
 后记
后记 这本书半数以上的文稿曾经在《安顺晚报》文化副刊上登载,从2006年11月28日《徐霞客过安顺》首篇始,至2008年3月28日《杨树做官的二十个“不为”》止,共历一年零四个月。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又二年,我在撰写另一部红楼梦研究的书稿时,尚有与同人磋谈的“沙龙”意味的话,这次则是将双脚踩在了为之忙碌大半生的这块地上。
首篇“天涯孤旅”登出时,《黔山夜雨》栏目主持人唐明英女土曾寄语:
多情谁是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陆游《秋波媚》)古往今来,寄情山水的文人,在领略其中的光与色、情与景、人与事中,都会产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徐霞客过安顺》读来让人震动。对于读者而言,它的解读、分析、思辨都很有分量。徐霞客在人生的选择上,为何要以一生的代价,作“驱命游”,作“性灵游”,其间包含着多么深沉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