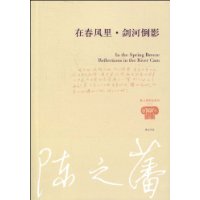|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在春风里·剑河倒影 |
 |
|
 |
在春风里·剑河倒影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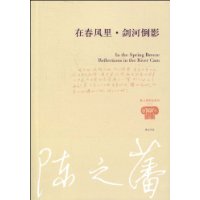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黄山书社
·页码:177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
·ISBN:7546102103/9787546102108
·条形码:9787546102108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陈之藩作品系列
内容简介 《在春风里·剑河倒影》讲述了:“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作者兼具科学家及文人两种身份,作品风格一方面有科学家不同角度的看法、说理透彻的剖析,另一方面呈现出文人清新淡雅的诗意,别树一帜。作者用独特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他在撰文纪念胡适先生时曾说:“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读作者的散文,也很难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风”里,体会着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深情与智慧。
作者简介 陈之藩,1925年生,北洋大学电机系理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理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两册,散文有Ⅸ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看云听雨》《思与花开》等。获选英国剑桥大学艾德学院院士、英国电机学会院士及台湾元智大学“桂冠文学家”。
媒体推荐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陈之藩《在春风里》
不知是哪位圣人创出剑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无时无地不让你混合。比如教授与学生混合,喝茶与讲道混合,吃饭与聊天混合……至于行与行问的混合,他们以为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搞抽象数学的到实验室做起实验来,女秘书造诣而上成为教授,你就知道这个学校之怪了。
——陈之藩《剑河倒影》
编辑推荐 《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为黄山书社出版。
目录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在春风里
剑河倒影
……
序言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
文摘 我左右看一看,只有两个颜色。西边全是红的,那是夕阳;东边全是绿的,那是校园。喷泉处处如金丝银缕,在绣一幅红绿各半的披锦。
车,逐渐涌来,人,一堆一堆的团聚,然而依然很少声音。这是一个繁华、美丽,而也寂寞的黄昏。
今天是毕业典礼的日子。典礼要在黄昏时举行。毕业是学生们的事,而在这样热的天,教授们还得披披挂挂一堆红红绿绿的东西,来尽量渲染这颜色已够灿烂的人间。
屋里太热,而会尚未开。在校园里散步,向东一堆西一堆的学生及家长们打打招呼。
“陈先生,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父亲,这是母亲。”杰克如此介绍,我握握他们的手。杰克的父亲一边抚摩他的肚子,一边继续说他对儿子的勉励的话。
“孩子,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所有的最大努力,以后要看你的了!”
“谢谢,爸爸。”
“孩子,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已尽了我们所有最大的努力,以后要看你的了!”母亲不折不扣的把话重说一遍,只是声音提高了好几倍。她是一边喘,一边擦汗。
杰克说:“妈咪,小些声音,大家全看我们呢!”
“母亲对儿子说话,有什么怕看的呀!”于是她又重新再说一遍,“孩子,今天是最后一天,以后……”显然这句话她是准备了好多日子的。
我一边拍一拍杰克的肩膀,一边将今晚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一个词,向杰克说一遍:“恭喜你!”父母给子女的叮咛是不变的,正如礼服的颜色是不变的;教师给学生的赠言是不变的,正如典礼的季节是不变的。而人却像河里的波浪,向前滚;像林问的花朵,向下落;像天上的雨珠,从云彩里来到泥土里去。
我在学生们的影子里,看到我的过去;在家长们的叮咛中,看到我的未来。在时间的长流中,往日的记忆与来日的梦想,似乎同时呈现在这校园的空间里。
我大学毕业那年,喔,已经十年了。十年前,那是多灾多苦的中国;十年后,这是多金多色的美国。而人间的寂寞究竟有什么不同?
十年了,十年前多像这目前。虽然我的大学没有什么典礼,我的家长没有任何人到校,我的校园里没有这样多的绿树;而却比这校园多些东西,是学校外围的城防工事,到处是铁丝网,是堡垒,是弹痕。我的学校如一只船板上的箱子,而那时的都市却如红海里的沉船。我毕业的那天前夕,还听到校墙外,人海浪潮的卷地?舀天与子夜里怆痛的呼声之此起彼伏。然而古今中外人事的荒凉,又有什么不同呢?
十年前,我在传达室里领了个文凭,肩着我的行李,迈过铁丝网,走出校门,四顾茫然。
“我到哪儿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