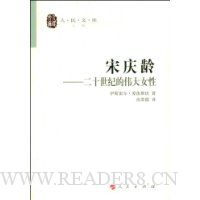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709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9月 ·ISBN:7010072167/9787010072166 ·条形码:9787010072166 ·版本:第1版 ·装帧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
 |
|
 |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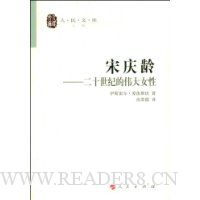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709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9月
·ISBN:7010072167/9787010072166
·条形码:978701007216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人民文库
内容简介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是作者受宋庆龄生前嘱托,历经十载完成的一部宋庆龄传记。书中全面记述了宋庆龄的非凡经历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充分展示了宋庆龄作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光荣的一生。书中关于宋庆龄的史实极为丰富,材料多是作者在与宋长期交往中亲身经历的或宋庆龄晚年亲自向作者提供的,因而真实可靠。《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是作者用英文写成的,由与作者长期共事的资深翻译家沈苏儒译成中文,文笔生动活泼,极富可读性。
目录 总序
中文版序
第一章 青年时代:美国,1907-1913年
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一)祖籍海南
(二)父亲宋耀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三)民族尊严和西方教养的矛盾
(四)虔诚贤淑的母亲倪桂珍
(五)成为企业家、爱国者和革命者的宋耀如
(六)宋庆龄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一)同孙中山的结合
(二)爱情·革命·理想
第四章 孙中山
(一)贫农的儿子
(二)“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
(三)从改良到革命
(四)百折不挠
(五)列宁的评价:革命民主主义者
(六)内心世界
第五章 为了维护共和:上海一广州,1916-1922年
(一)南下护法
(二)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三)支持五四运动
(四)作为非常大总统的夫人
(五)参加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谈
(六)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
(七)广州脱险
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
(一)《孙文-越飞宣言》
(二)同李大钊的交谊
(三)促进同中共和苏联蚵合作
(四)动员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
(五)历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六)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七)犯难北上:为了团结和斗争
(八)一代伟人的逝世
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一)化悲痛为力量
(二)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战斗
(三)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支持群众运动
(四)广州: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五)国民党“二大”:政坛首次表现
(六)从广州到武汉:迎接挑战
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一)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领土
(二)坚决回击蒋介石的叛变
(三)外国记者笔下的孙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妇女
(四)领导妇女运动及伤员救护
(五)在武汉的中外革命友人
(六)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七·一四”声明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一)决定性的行动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扰
(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第十二章 再赴欧洲:1929-1931年
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一)邓演达的遇害
(二)对国民党的“判决”
(三)营救牛兰夫妇
(四)动员抗日——1932年的淞沪抗战
(五)继续营救牛兰夫妇
(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七)谋害宋庆龄的阴谋
(八)抗议纳粹暴行——同萧伯纳谈话——反战大会
(九)30年代初期的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
(十)宋庆龄在家中
第十四章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高涨而曲折的潮流
(二)宋庆龄和1935年的学生运动
(三)帮助国共高层的初期接触
(四)鲁迅的逝世
(五)救国会“七君子”案
(六)宋庆龄和“西安事变”
(七)从主席台到监狱大门
(八)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从上海到香港
(二)不顾日机轰炸危险,数访广州
(三)反对投降主义
(四)三姐妹同赴重庆:为了团结抗日
(五)预兆不祥的“皖南事变”
(六)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而努力
(七)西方的战争:对东方的初步影响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与尼赫鲁的通信
(九)对日本军国主义——抗击到底;对日本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及其意义
(十一)战火蔓延,离港赴渝
第十六章 抗战岁月(下):重庆,1941-1945年
(一)摆脱国民党官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恢复保卫中国同盟
(三)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
(四)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工作
(五)不忘记老朋友
(六)史迪威时期
(七)统一战线——以及救灾
(八)在重庆时的生活
(九)充满危机的年月:1943-1944年
(十)亲属关系
(十一)史迪威去职——战争结束——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
第十七章 在战后的上海:1946-1949年
(一)和平或内战
(二)从保卫中国同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
(三)在新环境中保持老传统
(四)围绕着战后救济工作的斗争
(五)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友好
(六)把救济工作同重大问题联系起来
(七)周恩来的一封信
(八)给尼赫鲁的信
(九)建立反对内战和蒋介石独裁的统一战线
(十)在“超级”通货膨胀的压榨下
(十一)在上海为妇女、儿童、贫苦知识分子和未来而工作
(十二)面对谰言
(十三)在人民的事业即将获胜的时刻
(十四)黎明前的黑暗
第十八章 建设新中国:1949-1965年
(一)新中国的诞生
(二)在党政事务中
(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人民外交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中苏友好
亚洲的“亲戚”
对印度的情谊
对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越南:同胡志明的会见
日本和日本人:保持同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鲜明的立场、深厚的友情
(五)家常聚会
(六)她的刊物《中国建设》
(七)维护妇女权益
(八)“儿童是我们的未来”
(九)在国内各地访问
(十)面对疾病
(十一)对建国后十六年的评价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艰难的日子,1966-1976年
(一)历史性的悲剧
(二)狂飙初起
(三)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
(四)宋庆龄同刘少奇
(五)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悼念斯特朗
同斯诺重逢
1971年:关键的年份
(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痛悼挚友
恢复同国外的交往
(七)巨人的逝世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生活
幽居
病痛、安慰和忧思
两个女孩子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一)继续关心儿童、妇女
(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结论
(三)缅怀英烈、先贤和战友
(四)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
(五)同亲属的联系
(六)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
(七)在最后的日子里
同“邻居”的通信
“悼念李燕娥同志”
最后的题字和讲演
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易篑前后
(八)高风亮节国之瑰宝
哀荣、安息
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北京故居中的怀念
引用及参考书目
人名、地名、专名汉英对照表
译者后记
……
序言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总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象。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读者——去认识和了解宋庆龄的理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文摘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他写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压”。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后记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并且本书作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有着国际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努力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实于原文。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达、雅”的要求来进行本书的翻译的,即:力求正确地、充分地、明白地、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并尽可能提高译文的文字水平。当然,这只是我为自己悬的鸽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所能说的是,我已在主客观条件和近两年时间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方面,作者的勤奋、谦虚和一丝不苟为我树立了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因为宋庆龄的许多作品原来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当时和以后出现的中文本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体不一、版本歧出、讹误脱漏、译名混乱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校核订正是目前恐无条件进行的浩繁工程。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据最有权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新的宋庆龄文集正在编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带在此说明,凡本书提到的所引用或参考的中外书籍(不包括刊物)已编成书目列于书后,所以在注释中都只写了作者和书名。
书后另一附录是人名、地名、专名的汉英对照词汇。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属于常识范围的名词如华盛顿、伦敦、《圣经》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读者查阅。许多人名的中译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广泛的或符合标准的译名,在对照词汇中列出其他我所见过的中译,以期将来能趋于统一。
有一些名词或外国人士和事物为英文版读者所熟悉而未必为中文版读者所知道,为便利后者,都加了译注。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为中文版读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读者不熟悉,从而在英文版须详述而在中文版则可适当简化。但考虑到中文版读者中将会有许多青年(以至少年),他们对于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的人和事未必知之甚多,所以这种简化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还有一个情况须稍加说明。为了希望本书中文版能与英文版都在1992年内出版,所以翻译工作(特别是后面的若干章)几乎是紧跟着写作进行的。爱泼斯坦同志的写作态度向来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总要反复斟酌,所以我估计本书英文版的最后付印样一定会同我所据以翻译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处,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爱泼斯坦同志的意见,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为准。(如有实质内容上的改动则照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轩同志,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张爱荣同志,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及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滩》杂志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孙源、侯寒江、陈廷祐、安淑渠、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纪青、陈日浓、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黄浣碧(爱泼斯坦夫人)等都曾在我的翻译工作中给以各种不同的帮助,谨致深深的谢意。我也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叶建华同志的合作。最后应该感谢的是妻子壁莹,没有她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对本书中译本的批评指教。
沈苏儒
1992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