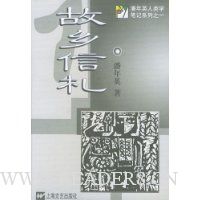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页码:229 页 ·出版日期:2001年01月 ·ISBN:7532121755 ·条形码:978753212175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故乡信札 |
 |
|
 |
故乡信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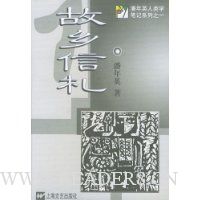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页码:229 页
·出版日期:2001年01月
·ISBN:7532121755
·条形码:978753212175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
内容简介 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钱,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
——韩少功
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它是否带有几分怀旧感?或许有些。在我看来,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潘年英的写作,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质,其属于中国文化边界旁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有其独到的魅力和价值。
——(法)安妮.居里安
作者简介 潘年英,男,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先后加入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学术团体。1994年荣获庄重文学奖,1997年3月调厦门大学任教,1997年获贵州省民间文学奖、广西民间文学奖,2000年获首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 主要著作有:《我的雪天》(1993)、《民族、民俗、民间》(1994)、《扶贫手记》(1997)、《边地行迹》(1999)。
媒体推荐 自序
在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黄昏,我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说不清这是第几次回家了,但每次的情形仿佛都一样。先是从我现在居住的那座繁华的城市乘着火车赶到地区州府——一个有名的叫做“凯里”的地方,再换乘公共汽车到县城,这要耗费一天的时日,得在县城住上一夜;次日则再乘农公车赶往一个叫南明或石洞的小镇,实际则不到镇上,只在中途下车,然后沿一条小溪溯流而行,走路回家。大约走上十余里山路,则可见两山峡谷之间的一个小村,山青水秀,木楼簇拥,那便是我的衣胞之地,我日思夜想的家乡故土——盘村。
也许同别的一些“故乡”相比,我的故乡是不值一提的,地方偏僻、狭小、遥远,千百年来也从未出过任何使地方闻名的物产或名人,说起来,这地方没一样是值得我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东西。但是,上苍却安排我出生在这里,而且在这里度过了我苦难的童年时光,直到十七岁考取大学才离开。说来奇怪,从上大学到学成毕业后留在那城市,到如今我在那城市也一样生活过了十七年,而那城市却无论如何不能叫我有丝毫的怀恋,或者说,我一点也没有把那个我同样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城市看作是我的“故乡”或所谓的“第二故乡”——老实说,对那城市,我不仅不怀恋,而且简直是憎恨的。
然而使我感到矛盾的是,我虽然爱着我的那个童年生活过的“故乡”,但我却不能再回到那里去谋求生存——我每每回家,把无限的情感倾泄于一次次疲惫的旅途,我明白这当中只是寄托着我的爱和理想罢了,倘是真正地生活下去,怕是不能够的。这无关技能方面的事,我童年时代也曾在这里学习过一切农活技艺,且操练得相当不错——关键只在心灵;那时候,我同样是没有半点安心的,我是如此地向往着早日逃离这个狭小的天地,梦寐到城市去开拓一片新的生存空间——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我却不能热爱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我一面咀咒着,一面却心安理得地生活下来,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
夕阳冉冉;故乡的山水沐浴在一片美丽温暖的氤氲之中。小桥流水,炊烟袅袅,到处是金黄的稻谷和抢收的乡亲,山坡上则有暮归的牛羊和隐约的歌唱——这情景是历来如此的,于我是司空见惯,但也还是感动。同行的徐君则很是陶醉了。徐君是我的好友和同事,他正好从小生长在我们所共同谋生的那个城市,专业是文学和人类学,如今已是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大教授大学者了;应该说,因专业的关系,徐君是经常下乡做所谓“田野作业”的工作的,因而对乡村并不陌生,但徐君对于我的老家故乡却有一种格外的钟情,也十分羡慕我能拥有这样的一处“故土”。我明白徐君说这话当然绝不止是称羡而已。
人类学近来有所谓“本土研究”与“异地研究”的争论,虽然从理论上讲二者各有优势和不足,但如果二者的知识背景相同,则是我更倾向于相信“本土”人类学者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就是“异地研究”的学者很难做到像“本土”学者那样对文化背景有一种“吃透”的深刻。事实上我也见识过不少“异地研究”的报告,当然,他们研究的精神还是令我感动——他们也像传统人类学一样,到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去,与那里的民族同吃同住,认权威的年长者为“干爹”或“干妈”,而且刻苦学习他们的语言,如此一年两年,他们写出了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研究报告,但恕我不恭吧,这当中的许多报告,与其说在做研究,还不如说是在做一种猜谜的游戏,或者说这往往都只是一些隔靴择搔痒、隔岸观火式的空洞华丽的文字,而根本无法触及文化或事物的本质。因而对于这样的研究,我见识多了,大约也有些麻痹,乃至于不敬。
……
编辑推荐 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钱,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
——韩少功
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它是否带有几分怀旧感?或许有些。在我看来,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潘年英的写作,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质,其属于中国文化边界旁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有其独到的魅力和价值。
——(法)安妮.居里安
文摘 书摘
我差不多到中午才回到家,这时猪早已侍弄好了,伙房里几位帮忙的屠夫正在吃泡汤,其中一位大约喝了不少酒,有些醉意了,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并叫我去跟他们吃饭。我认得出他便是我父亲过去的酒友之一,一个叫老灵的顶没出息的庄稼汉,昨天晚上我才听母亲说,他的两个刚刚长大的女儿被同村的老元拐卖到浙江了,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母亲抱怨我去了哪里这半天也不见影子,说一家人到处找我吃饭找不到。侄儿丁丁和当当报告说我去了屋背坡,母亲叨念说我每次回家都要去屋背坡转一圈,那屋背坡难道有好风景?
我不理会她们,自个儿躲到客房里去。
Nyo,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新房子的故事,这是我和父亲一起修起来的,说起来并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却也颇显陈旧了。那时候我还在天柱念高中,暑假回家,父亲便叫我跟他一起到
遥远的“高他塘”去砍木头,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些伐木的日子。天一亮我们就出门,一直砍呀砍,砍到中午太阳当顶,二弟和母亲才为我们送来米饭,但丢下斧子我就躺倒了,明知肚子饿得厉害,却无胃口去吃饭。看着我手上肩上的那些血泡,母亲心疼得流了泪,她劝父亲不要叫我砍木头了,说我还是孩子,造孽。可父亲说:“他不做谁做?请人做不要钱?”又说:“我像他这样大的时候,比这大几十倍的木头都砍过了。”又说:“做来还不是他们坐,你怕是我坐?我坐现在这栋就够了,我是怕他们三兄弟以后打架,才来吃这份劳苦。”
“坐”就是“住”的意思。
在整整一个夏天里,我就这样一直跟着父亲砍木头,剥木皮,扛木回家,累得像死去一回似的,但并不抱怨,我那时有一种决心,便是立誓要当盘江地方最让人看得起的农民,因为那
时我对于考大学还没有丝毫的希望,尽管我也好学,勤奋,且十分地巴望着能跳出农门,但一切都还十分缈茫,班上五十二位同学,我的综合成绩排在二十名之后,而老师说,只有进入前八名,考大学才有希望。
父亲看着一身伤痕的我说:“要想过安逸日子,那就只有一条路,读书,考大学。”
考上大学又怎样?我那时竞连设想也无从设想。父亲说:“考上大学,那就是国家干部了,吃皇粮,坐印子屋,不晒太阳不淋雨,像你庚爸运中一样。”
“印子屋”就是“砖瓦房”。“庚爸”就是与父亲“打同庚”做结拜兄弟的朋友。运中是他的中学同学,两人关系非常要好,父亲后来因为奶奶病故而中途辍学,运中却读书出了头在
凯里一家机械厂当了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