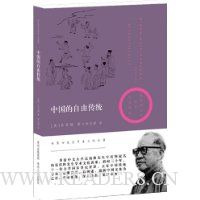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 ·页码:16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 ·ISBN:7221085110/9787221085115 ·条形码:9787221085115 ·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中国的自由传统 |
 |
|
 |
中国的自由传统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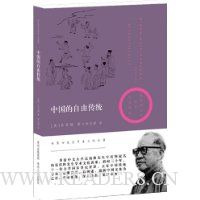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
·页码:16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
·ISBN:7221085110/9787221085115
·条形码:978722108511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内容简介 狄百瑞就中国宋明理学的传统讨论中国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特质。《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论及新儒学“学以为己”的个人自发色彩,其强调自得,相互激励等价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识分子自任于天下的责任感,认为黄宗羲正代表了这种自由主义特质的新综合。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最后一章中,狄百瑞并讨论这种自由思想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
◆ 讲座及丛书概况 ◆
1、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由钱穆(字宾四)先生于1978年首次开讲,先后有李约瑟、小川环树、狄百瑞、朱光潜、陈荣捷、杨联陞、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等十余位中外大家开讲
2、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整理成系列并出版,每位演讲者一讲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首次与内地出版机构在大陆地区合作批量出版学术文化著作。
3、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探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扬学术风范,培养文化风格,自首次开讲至今,讲座的内容与影响均获得海内外学术界之重视。
作者简介 狄百瑞教授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1971至1978年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推动了东亚图书馆的翻新及扩充工程,建立乐人文研究中心,以及这中心辖下的人权研究中心。1978至1986年间担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主席。除了他在教育行政上的贡献外,狄百瑞教授的学术成就亦广被承认。他先后在1974年和1999年获选为美国文理学院和美国哲学会院士。狄百瑞教授的研究兴趣是东亚的宗教和思想传统,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儒学。他把新儒学研究引入美国,提倡一种对亚洲在通识和核心课程中的位置的全新构想。他在近年撰写和编辑的超过二十五部著作里,主要处理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人权问题。
编辑推荐 《中国的自由传统》: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香港中文大学以钱穆先生字(宾四)冠名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跨时三十年,仅十一位大学问家登坛开讲,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放眼世界,以阐述、创新中国文化为己任,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见解卓然。
专业书评 自由是个过时的概念
——简评《中国的自由传统》
法兰西曾是近现代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在这里,《自由引导人民》的画卷和自由女神像成为近现代光辉的标志。这些光辉仍在,但每天大谈自由的人当中,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五压根儿不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在中国,这个舶来名词是如此的含糊不清,又是如此敏感与脆弱,一些人只好拼命把它塑造成为概念木乃伊……现在,到了该跟这个木乃伊说再见,让它躺进博物馆的时候了,让我们用更加准确的语言来描绘个体、群体的追求吧。
狄百瑞先生的《中国的自由传统》就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因为当他开始描绘中国之时,以他的学养完全意识到,用西方的词汇来描绘东方会产生的误解,因此他采用同事弗兰克的提法来构筑全书,那就是几层意义上的自由:
1、与地域观念和宗教狂热相对立的文化自由主义;
2、政治自由主义;
3、经济自由主义;
4、哲学自由主义;
5、由中庸、自制与妥协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性格或风格;
6、自由的教育
……
在做出明确的层次的定义后,中国有没有自由传统也就不再成为问题,问题只在于,中国的自由传统在各层次意义上的表现。作为儒学的研究者,狄百瑞先生主要从儒家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阐述,这未免有些遗憾,因为在中国文化史上,道家、佛教在各层次上也各有其思想表现。
但单从儒家的角度,已让人感悟到其中的精彩。一个显著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自由观是分开叙述的,意志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由于儒家的入世精神,强调了个体与群体的融合而非分离——类似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从而其自由层次强调了个人的自觉,并通过具体的学习、生活、做事来体现自觉。孔子自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试问,谁能否认孔子的这个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呢?可见,追求自由本身就是一个自觉逐层级提高的过程。
正是这种深植于个人修养中不断精进的追求,才造就“更多层次的自由”,须知这些“自由”从来不是来自赠与或者恩赐,更不是掷色子的游戏,而是来自自我的判断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这个孤零零的名词,实在应该做些准确定位的修饰了。
目录 1 引 言
1 第一讲 人之更新与道统
19 第二讲 朱熹与自由教育
53 第三讲 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93 第四讲 明代理学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
131 第五讲 自由主义的局限
151 附 录 迎狄百瑞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金耀基)
164 译后赘语
……
序言 当我接到邀请承乏1982年度的钱穆讲座时,虽然很怀疑我是否能勉孚由中国学术界中这个伟大的名字所激起的期望,但被邀约来参加这个声誉卓著的讲座,这项殊荣本身就足以使我接受了。而且,我也有着强烈的个人理由来承乏这项责任——过去许多年来,钱宾四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任何人接到以这样一位久施教泽的师长为名的邀请时,当然是不会加以拒绝了。
在我心中钱穆先生杰出的学术贡献与17世纪的一位学者黄宗羲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我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之后不久,黄宗羲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已是1937至1938年间的事了,当时大多数人都以为只有从事与传教工作有关的人才会想研究像中国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题目。但当时在纽约及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正如同宗教一般,具有政治色彩,我和保罗?罗布森(Paul Robeson)及其他同学,他们的言论激进,我与他们一样也同情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具有一种年轻人的热情。后来,当我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目睹欧洲的变局后,开始有了觉醒——斯大林的整肃行动出卖了革命的理想,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协定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更形放肆,纳粹军队宰割了欧洲,四处屠杀犹太人;再又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等等。我对那些主张拿西方式的革命来解决中国困境的办法就不再那么乐观了。我开始探索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与历史,也许它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免于受革命与反动之苦的未来。
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当时尚不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黄宗羲。20世纪初,黄宗羲是中国变法家及反清革命家心目中的一个英雄。那些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民主价值的人称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虽然他们很少把黄宗羲的思想与民主价值作深入比较,也很少从黄宗羲的时代背景中详细分疏他的思想。后来,当“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平地而起,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从中国历史中完全解放出来的时候,革命的浪潮就把他们这种儒家的温和改革思想冲到一旁了。
就在这个关头,钱穆先生进入了我的心中。钱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正如钱先生后来在本讲座所再度肯定并细加分疏的观点一样,中国千万不应该想要用那种从根拔起并摧毁过去遗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解放;它只能透过中国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坏都面对它,认为中国人的未来实植根于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虽然有些中国人可能寄寓异国,并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历史所形成的条件与外观之下。对他们来说,移民异域当然是不可能的[1]。
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钱先生早年曾重新疏解新儒家的史料,并且从宋明及清初思想史的立场来覆按黄宗羲思想的脉络。我发现钱教授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我在太平洋服役,开始研究黄宗羲其人的思想史著作的时候。钱教授在其所撰17至19世纪思想史的书序中,提醒读者注意宋代新儒家思想的渊源[2]。
黄宗羲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2年,正是他从抗清运动中归隐不久的时候。在这部批判明代专制政治及其腐化的著作之中,黄宗羲强烈地表达了他在朱明王朝参与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以明代遗老身份抗清的双重挫折。作为明朝忠臣,黄宗羲耿直地批判明廷的缺点来为朝廷尽忠(儒家意义下的尽忠);同时,身为一个对历史有广泛认识的新儒家,他对于朝政的败坏也详加分析,并远溯其根源,迄于远古。
黄宗羲的学术努力可能是近代以前对于中国专制政治所作最整体而有系统的批判。这部书的确对传统帝制作了激烈的攻击。虽然黄宗羲痛诋的是政府,但是继起的清朝却也觉得这部书对他们具有威胁与倾覆的危险。我认为这部书由于它在史学素养上的广度,在道德感上的深度以及表达方式上的雄浑有力,可说是儒家政治思想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职是之故,黄宗羲的著作在这些方面几乎自成一格,但我们却也不可以认为此书完全特异而与众不同。黄宗羲并不是一个切断他的过去,与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格格不入的孤立的天才人物。相反的,黄宗羲的抗议只是把他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政治观点作比较明确的表达而已。他这篇激越的宣言虽然因为朝代板荡与外人入侵的危机而深刻化,但这篇文字不过是新儒家自由传统发展中的一个高潮罢了。这个传统是黄宗羲乐于认知并重新加以肯定的。
然而,这部著作并不是黄宗羲论述明代的最后一部书。黄宗羲不是只会指出明代的鱼烂局面,却将自己置身度外的人。他晚年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阐述明儒在思想及文学上的学术业绩。这些晚年工作的代表就是《明儒学案》。它是明儒思想的批判性的文集,后来更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为后人所效法(甚至撰述《朱子新学案》的钱穆亦同)。黄宗羲在此部巨著的卷首识语中曾说,有明一代虽有缺失,但是明儒在理学的中心领域里,却获得了卓越的成就[3]。
对我们而言,这种说法所具有的意义不止一端。表面上,黄宗羲所编的巨著可视为一种保守性的努力——一个典型儒家学术守先待后的例子。但是,既然黄宗羲对明代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么苛刻,我们就更不可把他对明代的哲学成就所作的推崇视为当然,或径贬为泛泛夸赞之词。尤有进者,黄宗羲所持对明代思想的同情态度——认为保存明代思想具有积极的重要性——正与清初学者(17世纪下半叶)对明代思想所持的流行看法形成对比。当时人认为明代思想空疏腐化,最好与亡明余烬一起烟飞灰灭。真的,黄宗羲所必须阻挡的反明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就此点言之,黄宗羲在“保存”明儒思想遗产的努力中,实已采取了一个与当时思想主流相抗衡的独立立场,而且与当时官方的观点也当然是互为凿枘的。
后面我还会谈到有关黄宗羲这项决心的更深刻的意义。但我愿在此说一些或许不是题外的话:就是到今日,像钱穆先生的学术也仍须面对新儒家思想的敌视态度,甚至要面对政治上对儒家思想的激烈攻击。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因此我认为钱先生也继踵了黄宗羲的典型,保存(虽然不是绝无批判地保存)了他的新儒家的遗产。
当黄宗羲谈到明代理学的时候,他指的是那股远溯宋代(960—1279)的思潮中的一个特别的阶段。其后当黄宗羲编完《明儒学案》之后,他更把时间上溯到宋元两代。可惜直到他过世之时,仍未完成《宋元学案》的编辑工作。《宋元学案》这部书里的“理学”涵盖了整个源于宋代的广袤的儒家思想,以宋代为其形成期而绵延及于元明两代。很明显的,在17世纪末叶,黄宗羲仍指望他所如此心仪的明代思想能在花朵绽开之后,在他自己的时代或后世结成果实。
近代西方使用的“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这名词,正如冯友兰、卜德(Derk Bodde)、张君劢以及我们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儒家思想研究丛刊》各书中所使用的一样,一般说来,是与黄宗羲所指的这个新思潮相通的。也就是说,这个名词包括程朱学派,也包括所谓陆王学派的理学思想(我说“所谓”是因为陆象山与王阳明在某种程度上有其相似之处。虽然王阳明事实上是明初的程朱学派所衍生,而与陆象山之间并没有可以上溯到宋代的学术脉络可循)。对黄宗羲和其他新儒家的史学家如孙奇逢而言,“理学”这个学派包括陆象山与王阳明[4],而“心学”则同时泛指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
最近,有些西方学者由于受某种争正统的态度的影响,把“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一词用来专指程朱学派及他们所说的“道学”。但是,很清楚黄宗羲是反对只有程朱门人得道的说法的。他也反对只把“理学”局限在“道学”的范围之内[5]。因为程颐与朱子始创“道学”一词,所以用这个名词来指称程朱学派理当有其历史基础。尤有进者,程朱学派之作为正统思想已为后来中国、韩国及日本许多新儒家所接受,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道学”或程朱学派称为“正统新儒家”。然而,如果把“理学”或“新儒家思想”这个名词仅用来指程朱学说,则此用法实与“理学”的历史不符,而且与习用的“新儒家思想”这个名词的用法存在分歧。
在这里所遇到的名词上的问题并非无关宏旨。它们均涉及我在这几次演讲里所要提到的中心课题。因为黄宗羲在面对这种狭窄的新儒家的定义时必须两面作战——他一方面反对那种以褊狭的正统自居的保守、独占而权威性的态度;一方面又反对那些弃绝“正统”、认为传统已濒败灭、无关紧要的人所持的轻蔑的反动态度。换句话说,兼具史学家与哲学家的身份,黄宗羲致力于对新儒家思想作更磅礴、更自由、更具有活力的解释。
在采用“自由的”(“liberal”)这个字时,我当然必须预料到其他误解的可能性。有的人根植于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代表的)对自由主义采取狭隘而纯粹的定义。有的人则认为自由主义带有一些他们以为是源自西方的放肆的特点。这两种人都曾认为把自由主义一词加诸中国是陌生而不切题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值得冒一下险。真的,只要不排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探索其相似点,并由此而对双方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的相异处作尽可能完整的讨论与分析。
几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举行的一项研讨会上,我已故的同事弗兰克(Charles Frankel)——他是美国自由主义及人文学界有力的发言人——就曾经从七层意义上来诠释自由主义一语。今试加撮要如次:
(一)与地域观念和宗教狂热相对立的文化自由主义:“对提升心智的多面性及其品质有肯定的兴趣,以便能对人类生活的种种可能性作同情的了解及批判的欣赏”;(二)政治自由主义:“对于能将和平变迁加以合法化的程序加以强调”;(三)经济自由主义:“为纠正经济力量的不平衡而制定的政策”;(四)哲学自由主义:“相信理性探究方法的优先性”;(五)由中庸、自制与妥协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性格或风格;(六)自由的教育:“对于长远的道德理想、文化理想及文明理念抱持有实践的信念,并且能妥协而不哗众取宠”[6]。
在儒家传统中找到与上述各项相对应的说法或态度并不困难,但是任何认真探讨,希望作满意的比较,都应该涉及两者之间的重要不同,即儒家的自由传统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之间其相似性也必须大打折扣:例如上述第四项所论及人在探讨问题时应该把理性方法视为第一要务这一点便是。认清两者间的不同对于认识两者的局限性会有启发。
儒家之教训深寓人文色彩,认为人在改变世界之中扮演着最重要而且具有创造性的角色,因为孔子把人的生命与经验视为一切可靠的学问之焦点。“人文的”一词在此的含义就是“现世的”(“this-worldly”)。但儒家并不把“人文”视为与天道相对之事物;相反的,孔子认为人事本身乃天道之显示。
孔子努力于保存传统文化的菁华,并肯定人类经验的永恒价值。在这层意义下,他可以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因为孔子认为过去的理想与典范可作为批判当代制度的基础也足以提醒人所秉承于天的伟大天赋,所以孔子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此所谓“自由主义者”一词可以是“改革者”的意思——敢于与现存否定人有实现其合理需求与欲望之机会的不公正政府相抗衡的“改革者”。这正是莫莱(Gilbert Murray)所说西方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相冲突而是互补的道理。他说:“保守主义的目标是拯救社会秩序。自由思想的目的是要让社会秩序更接近于自由人——免于自私、免于激情、免于偏见的人——所考虑为需要的境界,并且经由这么一点点改变更有效地拯救社会秩序”。[7]在孔子之后的时代里,儒家也都是改革者,他们提倡为生民立命的社会福利政策。
然而,孔子本人绝不是安于现状,耽逸自得的人。他说他自己乃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并以久不梦见政治上的理想人物与时代来策励改革而深自慨叹。人类对其他人的需要有作出反应的积极义务;因此就人君而言,无视于这种需要,实在是不仁之至。职是之故,儒家的改革主义实系渊源于对人类福祉的正面肯定,并由对于现阶段制度所取的批判态度来加以充实。后者反映了他们对于改革社会的其他可能途径的警觉。
有宋一代儒学的复兴所产生的新儒家思想也表现出相同的态度。但他们更把这种态度带到一个具有宋代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下文,我会用“新儒家”一词来指在宋代具有特质的这个运动中的要素(虽然这些要素未必不见于在此之前的时代里);我将继续用“儒家”这个名词来指那些相对地不具这些特质的永恒价值与态度(虽然它仍不可避免地与过去有某些形式的差异)。在这些新发展之中,我将集中讨论那些渊源于传统儒家但同时也朝着“近代的”、“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观念。我无法深入详细地追溯这些复杂的历史潮流,但为了方便这几次的演讲,我想讨论这些潮流中具有代表性的若干新儒家的基本观念。因此,我采取的是观念史的方法,在风格上很接近于钱宾四先生。我找出洋溢于宋明两代新儒家论著中的中心观念,间或提到这些观念流传于东亚的文化交流时日韩两国如何对待它们的情形。这些观念是整个新儒学(即黄宗羲所取广泛定义)必须时刻用之作为指涉者,不过这些观念本身则大体上出自新儒学思想的主流,即一般所说程朱学派或“正统”新儒家的思想。
首先,我应该说明一下宋代的学术趋势。宋代思潮重新重视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又具有新的批判性格。这两者一在重估过去、一在拓深传统,遂交互为用,以服务当代的需要。这些态度明显地表现在“道学”、“道统”以及“心学”之中。接着,我要讨论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教育与自发精神,这是宋明两代“自我”的广义观念以及独特的个人主义的基础。在此处,具有关键性的观念是“为己之学”、“自得”、“自任于道”以及程朱思想中与“自我”有关的观念,最后我要评论这些发展对晚明的影响。我并将归结到黄宗羲寻觅一个新的综合的努力。在我看来,这个新的综合代表了比较成熟的新儒家的自由主义。结论一篇有一部分来自于1979年11月我在哥伦比亚的公开演讲。它会就宋明这些思潮的发展与现在中国情形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注 释
[1]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第12-158页。(以下简称《民族性》)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1937,上卷,第1-7页。
[3] 《明儒学案》,万有文库本,台北:商务,1965,“凡例”,第一册,第1页。
[4] 孙奇逢:《理学宗传》,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影印1666年版,卷七、九、十七、二十一及二十六。
[5] 《明儒学案》,“自序”及“凡例”;并见其《破邪论》,一上下,刊《梨州遗著汇刊》,上海:1910,第十三册。
[6] Charles Frankel:“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刊所撰Liberalism and Liberal Education(《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ogram of General Education,1976,第3-11页。
[7] Gilbert Murray: Liberality and Civilization(《自由性与文明》), London:Allen and Unwin,1938,第46-47页。
文摘 自由仅仅是西方的价值吗?中国有没有自由的传统?很多中国人认为没有,但是西方人认为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自由传统》,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的。作者是研究理学的,他从儒家的“为己之学”、朱熹的《相约》等来论证中国的自由传统,未免过于狭窄。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我认为中国自由传统不仅存在于百家的思想中,而且在历史实践中。比如历来对宗教的宽容,就是多元文化的自由精神,对人类是一种伟大贡献。直到如今,世界上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还打得不可开交,然而这些宗教信仰在中国却能友好相处,而且历来如此。中国对文化和宗教的宽容,在国际上也有表现。二战中犹太人走投无路,中国驻布鲁塞尔公使在几天内给犹太人几千个签证,救活了他们。别的国家没那么大方。但是这种自由传统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结构的,我们没有发觉它。所以不必一提自由就认为是西方价值。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把自由当作价值来相信它,就是普世价值。一旦普及成为社会意识,就会释放人的巨大潜力。但这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研究,希望大家多指教,错误不妥的地方我可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