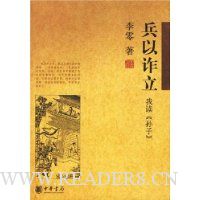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 ·页码:399 页 ·出版日期:2006年08月 ·ISBN:7101051340 ·条形码:978710105134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 ...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
 |
|
 |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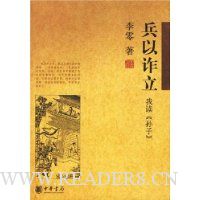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
·页码:399 页
·出版日期:2006年08月
·ISBN:7101051340
·条形码:978710105134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是一本在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讨论《孙子兵法》的书。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凭借20余年积累的古文献和历史文化知识,在讲解《孙子》各篇时,插入大量的背景知识,涉及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方面,令人目不暇接,为我们理解这一经典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子兵法》在兵法类的作品中出现最早,但其闳阔深远,却迄无超越者。此书真可谓集运用之妙的大成。在以往所有的军事思想家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之相比,但就连他,也比孙子要“过时”,显然有点古老陈旧,尽管他著书立说,比孙子晩了两千多年。孙子有更清晰的眼光,更深刻的见解,和可以垂之永久的魅力。
作者简介 李零,生于1948年,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徒张政烺先作周铜器研究。1982年华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至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澧西队徒事考古发掘。1983年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上地制度史的研究。一九八五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长期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放虎归山》、《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绩考》、《(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郭店札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简帛文献兴学的术源流》、《花间一壶酒》等。
媒体推荐 书评
这是一本在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讨论《孙子兵法》的书。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凭借20余年积累的古文献和历史文化知识,在讲解《孙子》各篇时,插入大量的背景知识,涉及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方面,令人目不暇接,为我们理解这一经典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推荐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这本小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为此,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希望读者喜欢它。
目录 自序
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一)《孙子》是一部兵学经典
(二)《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
(三)最低限度参考书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
……
序言 一
西谚云,战争是死亡的筵席(War is death feast)。
还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残忍,饥餐渴饮,自相残杀,
至今想不出办法,可以制止它。
以暴易暴,怨怨相报何时了?
可是,我们还要活下去——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
兵法是生存哲学,我这么想。
葛兆光说,李零有兵法,时常拿我打镲。
他请我到清华演讲,特意向学生这么讲。
司马迁说,孙膑、吴起不会保护自己,
就像商鞅和韩非,作法自毙,下场很惨。
中国,玩兵法于生活著太多,我是虽讲而不会用。
《孙子》是一部兵书。
但《孙子》不仅是一部兵书,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
智慧是个中性词汇,可以做各种解释,
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那就错了。
有人说,华人最滑。
其实,聪明过头,就是傻。
谭嗣同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飘渺间”(七律《题江标修书图》)。
最近,“尊孔读经”又成热门话题。
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
我的看法,中国的经典,不是没人读(五四以来,一直有人读),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读法和以前不一样,用不着哭天抹泪,说不读经典,就天塌地陷、亡国灭种,更不必瞎扯,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看在孔子的面上。
五四以来,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五经也各得其所。
这是好事。
如《诗经》,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尚书》、《左传》,也放在历史专业,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易经》、《论语》和《孟子》,则放在哲学专业,和《老子》、《庄子》搁在一块儿讲。三礼,王文锦先生讲课,是在我们的考古系。
经典,当一般古书读,本来就五味杂陈,是个大杂烩。近代,大卸八块.解构重组,这很正常。不是不读,而是换个方法读。
另外,打利玛窦来中国,400多年了,咱们的书,不光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比如国外的书店,汉籍之中,译本最多,要数《老子》、《周易》和《孙子》。《论语》是咱们的看家宝,翻译最早,但广大外国老百姓,读者寥寥,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
道理何在,值得思考。
近代,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一直有人讲:
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
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
现在的道德,更是糟之又糟。
贪官豪夺,奸商巧取,
老百姓也无心学好(光靠勤劳,只能当“杨白劳”),
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
当年,西方初遇中国,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第一是《论语》,第二是《周易》,第三是《老子》。三段论,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反而高级。他最看不上《论语》,说这本书,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读过原书,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就好了。
西化后的中国,我们有了“哲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
1930—1934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一上来,先讲取材标准,什么是哲学。日人高濑武次《支那哲学史》为兵书作提要,特别推重《孙子》,冯先生以为大谬。他说,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本书不能收,书中没有《孙子》。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才把《孙子》收进来。
兵法里面有哲学吗?
北魏,魏太祖不懂中国书,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说:“唯着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魏书?李先传》)。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
然而,1984年,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孙老韩合说》。他说,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中国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晨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韩非子》的帝王术,最后到《韩非子》,才“益人神智”,一字一句,“多么犀利、冷静和‘清醒’,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汉以来的儒家,外面是儒术,里面是这类东西,《易传》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
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
李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
今天,读经典,有两本书不能没有,一本是《孙子》,上面说了,最有智慧,百代谈兵之祖;一本是《老子》,教我们放下“人”的架子,别跟人逞能,要谈宇宙人生,老子天下第一。
这两本书很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连读带讲,一学期,正好。还有一本,也很短,是儒经中的《周易》,但《易经》本身,离开《易传》,也就没意思.加上《易传》,字数也不少。数术无经典,《易传》很重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它是必读书。《论语》,我也很重视,没有理由不重视,但不是学哲学,也不是学道德(我有《论语》讲义,另外讨论)。这书的篇幅大了点。上面三本书,《孙子》、《老子》和《周易》,全都加起来,才顶得上一部《论语》。其他子书,多是皇皇巨著,不选没法讲。
《孙子》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
二
说起讲授《孙子》,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
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北大,我是外来户。古文献,我是外行(累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
1986年,备课一年,我开始试讲,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
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上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能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总不能拉着别人听。走就走吧。
还有一个学生,叫魏立德(Franqois Wildt),岁数跟我差不多,法国来的,留在教室里,不肯走。他说,老师,他们不听,我想听。我说,就俩人,还占这么大个教室,太没意思了。你要听,就到家里来吧。
那阵儿,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没房,学校不分,我也不要。除了上课,不去学校。现在正好,彻底不去了。每次上课,魏立德都很守时,总是提前一点到,不到正点不上楼。我从窗子往外瞧,他在树下抽烟。
后来,他成了专家,真正的专家。他翻译过《三十六计》,在法国卖得很好。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他最懂法国理论,也最通中国兵法。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彰,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参看本书第七讲)。
1989年以前,学生经常不听课,在宿舍睡大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课堂里稀稀拉拉。他们还喝酒,我带的那个班,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后夫,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学校规定,酒不能喝了。但毕业是例外。为了庆祝,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我记得,有一个班,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碰杯时,总是说,谢谢您教我们兵法。我头有点重,但不及于乱,回家还能骑自行车,天不旋,地不转。
我觉得,他们只是客气。
这是往事,走麦城的事。
卖个破绽给你听。
凡是上我的课,我的态度一贯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人来人去两由之。
有个学期,我做过试验,把《孙子》课扩讲,不光讲《孙子》,还讲其他兵书,学生不多。
那学期,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一个是美国人,叫郭锦(Laura A.Skos—ey);一个是加拿大人,叫江忆恩(Alastair I.Johhson)。郭锦曾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到我家谈话,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孙子兵法)的讨论稿。后来,他做了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译本,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在申谢中,他说他曾受益于我。江忆恩,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美国,跟他通过电话。1995年,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他说,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崇尚有限战争,低估“纯暴力”,其实,它还有另一面。我的印象是,中国传统,确实不够凶蛮,但也不是“和平鸽”。
再往后,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Robin McNeaI)也听我的课,他在美国也讲兵书。
中国学生,我只辅导过顾青,研究《尉缭子》;还有张大超和田天,研究《六韬》。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写过不少研究《孙子》的文章,最近也来吁我的课。
1989年、1990年和1992年,我参加过三次《孙子兵法》研究会举办趵国际研讨会。这最初的三届,我都参加了。在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于汝波、黄朴民、刘庆等先生。地方学者,如可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北京的穆志超先生,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也是在会上认识的。还有吴九龙先生,以前就认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孙子兵法》研究会,要我担任理事,但我尸位素餐,以后的会议,全都没参加。
我喜欢业余身份。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有消息可听的会,我已不参加。
陆达节以后,许宝林、杨炳安、穆志超、于汝波先生,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对后学贡献较大,可惜不在了。
国外,对兵书感兴趣,有几位学者,我比较熟悉,如叶山(Robin D.s.Yates)教授和石施道(Krzystor Gawlikowski)教授。他们都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还有一位,我不认识。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教授的书,《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也很有意思。我从这些学者,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
二十年过去,我讲过多少回《孙子》,已经记不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
一是手中有书,心里不慌。我出了两本书:《(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这两本书,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基础是有了。最近,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稍加修订,取名为《(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进行再版,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
二是对时间的掌握,对语速的控制,比以前好一点。《孙子》只有五六千字,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稍微发挥一下,时间就满了。不能讲太多,也不能讲太少。有书,用不着满黑板抄。
三是我爱离开书本,东拉西扯。故事会,学生喜欢。北大老师,有经验之谈,千万不能编教材,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有书,学生不爱听,老师没法讲。我的理解不一样。我不怕出书。没书,一定要讲出本书;有书,正好神游物外,可以离开书本,讲很多有关的话题。课下读书,课上吹风,各有各的用。
我也是学生。
我是我最好的学生。
现在,学生很多,教室里,装不下,即使凑热闹的人走了,也还是很多。每次讲完,他们都给我鼓掌。
但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原来的书,是基础和毛坯,文献学的基础是有了,思想文化的东西还展不开,上课全凭一张嘴。
我不相信自己的嘴。
写作新书,我也考虑过,但不是眼前这本书,而是一九九九年许的愿,我要写本叫《兵不厌诈》的书。我想,同一主题谈两遍,是精力的浪费,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中华书局的领导徐俊先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整理。上个学期,他几次来北大,安排樊玉兰女史(本书的责任编辑)来我校听课,随堂录音,进行整理,让我非常感动。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算练手,朝目标再挪一步吧。
我这本小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为此,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
希望读者喜欢它。
2006年6月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文摘 书摘
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我们的前两讲是序说,主要是介绍情况。
孙子其人,我不讲。因为史料太少,没什么可讲,讲也是司马迁那几句话。社会上,争故里,瞎编胡说太多,一写一大本,都是骗人。
我只讲书。
在第一讲里,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要讲的这本书。主要讲一下《孙子》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经典化。这种历史,稍微有点枯燥,我劝大家要有耐心。它是一扇门,门是关着的。打开这扇门,你会发现,里面的院子很大,房间很多。
(一)《孙子》是一部兵学经典
中国的古书很多,现在怎么读古书,读哪些书,是个大问题。过去,因为西化的压力太大,启蒙的呼声太高,鲁迅故意说,青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劝伏案功夫未深的朋友,根本不必读线装书,非读不可,与其读经,不如读史,尤其是野史和杂说,读了才知道,中国历史有多么烂。这是一个极端。最近,风水倒转,有人又提倡读经,而且是少儿读经,少儿背经,从娃娃抓起,连蒙学课本都搬回来了,目的是借中国文化,重扬我大汉天声。这是另一个极端。两种态度,互相顶牛。
我认为,古书还是可以读一点,但不能代替今书。古典就是古典,就像供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我是隔着玻璃柜欣赏。现在,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结构已发生变化,经典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我认为,即便读经,也不必是原来的读法。首先,中国经典,不止儒经,还有其他很多宝贝,要读,不能光读这些。其次,经书,五经、九经、十三经,有早有晚,诸子百家熟知的六艺之书,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典化。经典化就是古董化。如《诗》、《书》、《易》三种,早就是古董,汉代,大人都读不懂,何况少儿乎?汉代小学,主要读蒙学课本(识字课本),即《苍颉》、《急就》,和《三字经》、《百家姓》差不多。这些读完了,再读点德育课本,《论语》、《孝经》。《论语》、《孝经》,本来是子书,汉代不算经,只算传记。传记和子书同类,也叫诸子传记。五经太深,小孩不读。我看,今天读古书,子书更适合。如果读,不妨从《史》、《汉》入手,由《史》、《汉》进读子书,由子书进读更难的书。让小孩背诵,还不如背点诗词。
西方人读中国书,他们有挑选。书店里,我国典籍,名气最大,是代表中国智慧的三本书:《老子》、《易经》和《孙子》,很多老百姓的家里都有这几本书。孔子是咱们中国的大名人。人,他们都知道,但书不一定读过,主
……